《十二雕窗檐下燕》正在更新中。桐城盛夏蝉鸣聒噪,手工乐器铺老板杨伦用沉默藏着过往。失聪的快递员贺长青送包裹时,总带来如风的温柔。这里的时光很慢,慢到绿豆汤熬足一天,二胡磨够三月,也慢到杨伦愿意用余生,去修补贺长青那颗曾伤痕累累的心。夏去风未停,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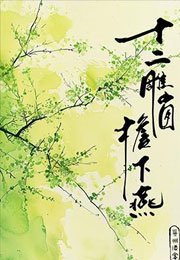
《十二雕窗檐下燕》精选:
黄昏吝啬洒下斑驳的光斑,垂照废墟中的眷侣。
石窟下,杨伦与贺长青如两尊泥塑造像,紧紧相拥。
风声清软,不舍得插入拥抱间的罅隙。这一刹时光被子规悲啼拉扯到亘古漫长,没有人舍得轻易松开双手。
这短短的十数分钟,写下如此之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说爱,第一次接吻,第一次直面死神。
当这个拥抱在万籁寂静中落成,杨伦感受着怀中温度,方觉后知后怕。他从未有任何一刻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他这样害怕失去贺长青。
他庆幸自己尚有一身好力气,能挡住世间风雨。
好在,好在。
杨伦已经泛起黑雾的视线飘向高空,心底颂了一声佛号。
若是造化有意提点,下次,不要再让贺长青一同犯险了。
千般业力,都让罪业累累的弟子来挑罢。
他骤然脱力,不自制地向下一滑。
“杨伦!”
贺长青心尖猛地一揪,双手去承托腋下,这才看到杨伦两鬓已是冷汗涔涔,把泥泞都打落不少。
杨伦揪住贺长青的手臂不让他去看身后的伤,单这一个动作,脸已经因为失血和疼痛而生白,单腿跪进泥泞才没有直接倒地。
“走。”
他冲贺长青安抚地一笑,手撑膝盖重新挣起身子。
贺长青拧着脖子去看他身后,却让杨伦握住下巴,又深深覆上一个珍重的吻。
他们两人独处时总是寡言,此时两片安静的唇碰到一起,似是有千言万语在耳边呢喃,反而吵闹起来。
直吻到气喘,四目相对,除了相视一笑,又何必再赘述。
他们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下跋涉。
转身时杨伦不经意向后回望,山体的滑坡并不算大规模。除却伐木场的这一片荒芜,其他未经开采的丛林土壤仍然被根系牢牢固定。看着这一片郁郁葱葱中的黄土弥漫,让杨伦不禁在肚子里频频苦笑摇头。
那是盖庙的梁,填瓦的土,是信仰背后的剥夺。
佛门清地,也免不了顾此失彼。
自然的平静来自对稚子的包容。
百年的树,千年的青岩,万年的冰川和亘古昆仑。讲述过一族又一脉的兴旺,也记载每一个短暂的路过。无声无息,穿岩凿壁。身怀古老秩序和雷霆撼地的力量,却原谅每一次打扰与加害。
终归是苍生自食恶果。
走出百步,当杨伦看到一尊半掩在泥浆中的残破文殊造像,他的嗓子里颤巍巍呼出一口热气,轻轻推开了贺长青。
杨伦躬下身跪伏在地,粗粝地手掌抹去慈眉善目上的泥泞,双手合十,上摊,虔诚三拜。
袒露在贺长青眼中,他的后背已经残破不堪。黑色的长衫被横纵交错的划痕剐烂,露出鲜血淋漓皮肉。破口从后脑到大腿一路层层叠叠。最深的一道在肩头,从左肩一路划到腰,深几见骨,似是把人一刀斩断。
可杨伦浑然不觉,在贺长青泛红的眼眶中动作规整,肃穆如一尊受难的罗汉。
他虎目迷蒙,拜叩的是众生妄为,是浮华不知罪,是百年难求双全法,是这一段离经叛道的情深。
他被贺长青搀起,轻轻点了点耳边的助听,脸探到贺长青看得着的角度。
“听不着了?”
方便贺长青读唇,他说得缓慢。
见满面关切地贺长青点点头,杨伦缓缓笑开,指了指山下。
“走吧。”
他们绕过残损的佛像,长风自山巅席卷。
“第一次在小院儿见你,我想着,这小孩儿真不懂事,话也不会说,和哑巴一样。等你帮我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你的助听,我当时真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走上崎岖的山路,曲径幽深。杨伦比贺长青高出一个头,唇在他的耳侧翕动。
“第二次是在快递点儿。我瞅着姓李那小子跟你动手,一想到你耳朵不灵便还得受这窝囊气,比你还生气。冲上去就想打人,那时候还没喜欢你,就单纯心疼。我想着,都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事后想想,估摸是挺给你添乱的。”
山脚下梵音千里,暮鼓声阵阵,涤荡在寂寥山间。
“那次加了好友,你给我发表情。我还琢磨这是不是笑话我呢,阴阳怪气的。但瞅你用皮卡丘当头像,我又觉着,这小子能喜欢这傻不愣登的黄皮耗子,那应该没有坏心思。”
这一处地势陡降,杨伦半脚打滑,贺长青连忙拽了一把,抻着了他没好透的伤手,俩人都是一阵龇牙咧嘴。
“第三次是来我院儿里吃包子吧。和小程警官一道儿来的,你呲儿我俩没吃相,他非得拉着你比划。警官人是真不赖,就是人来疯。你拿竖笛吹了一管儿布列瑟农。好听啊,那尾音撩的,心都跟着颤。我说这小孩儿有点灵气,家里养得好。”
路边不知怎的落下一块没抛面儿的六道木,比小臂略短,估摸是运输时候不小心掉的。贺长青捡着宝似的两眼放光,回头看杨伦,见他点头,立马用脚勾起来揣进屁股兜。
两人继续向前。
“再后来是怎么着...对,你联系不上我,上我家来。耷眉丧眼地说让扣钱了,哈哈。那小丧门星样儿,真是钻钱眼子里了。”
他一笑,连着腔子也震。贺长青偏头递来一个询问的目光,而杨伦含笑摇了摇头,在他看过来的时候短暂地闭上了嘴。
“然后你给我脑门上啪来了一水晶贴画,现在还搁桌子底下压着呢。可惜房子卖了,桌子得搁库房吃灰,回头我得记着给它撕下来。你告我,奖励给好孩子。你走了之后我就摸揣着那玩意儿琢磨,是啊,得当个好人呐。仔细想想,大概是从那时候喜欢上你的。呵,挺没道理你说。”
两人走出这么一程都有些气喘,稍停下脚,倚着树歇息。杨伦眼前一阵阵发黑,他用拇指肚摁了摁贺长青脸上让碎石划出来的血印子,有点儿心疼。
贺长青跟个小泥人儿似的,安安静静不吭声,和初见时那只知道摇头点头后生的身影叠到了一块儿。
杨伦心里的声音发涩。
我给你刻了个章。你告诉我,自己是个没爹妈的领养来的孩子。
其实杨伦想让贺长青再缓缓,但感觉浑身发冷,有点儿等不起。歇了歇,撑起最后的力气,一只膀子掸在贺长青后脖子上继续向山下挪。
“去芙蓉吃饭那次,我问你喜不喜欢雷曼。问完我一手心冷汗,得亏没让你看着,丢人。那会儿我就开始怕了,带你去见二哥,其实是想着但凡我出事了,让他护着你点儿。但进门看见你眼睛我就后悔了,我想着,要我不在了,这水晶贴画一样亮的眼睛得瞅谁去,我得吃醋喽。我就后悔了,后来琢磨,我那时候就想跟你过一辈子,到阳光底下去。”
贺长青的余光瞥到杨伦的嘴唇在动,偏过脸问了句。
“你说什么?我现在听不着。”
杨伦瞅他一眼,在耳根子上亲了一下。
“没说话。”
从山西一路行至山南,已经遥遥可以看到来时采购木料铺子的红顶。
“你叫我留头发,带我去见了你妈妈,问我是不是GAY。我那会儿光顾着替你难受了,脑子都是懵的,况且哪想过喜欢上一个爷们儿。但瞅着你一个人往剧场外头走,我心里头那叫一个......我当时就想,再不让你一个人那么走了。”
橘红色的霞光涂抹在木料铺子小屋的外墙上,堆叠在屋外的木料披上一层宁静而温暖的光晕。
杨伦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犹在絮絮叨叨不停。
“你说,你挡刀做什么。扎我一下也就一个窟窿,你那手可得留疤了......”
杨伦硕大的脑袋骤然一沉。
他的身子骨哪里是贺长青架得住的。杨伦向前扑的瞬间,贺长青也跟着跪在了地上。
“诶呦!天爷,这是怎么了!?”
正拎着扫帚从屋里出来准备清扫的老周一眼看见他们,惊得一把扔开家伙,冲上来扶人。
“...泥石流。”
贺长青喘着粗气,和老周手忙脚乱地先把杨伦放展,用手勾着他的脑袋。
老周一打眼两人身上泥泞不堪,伤痕累累,扭脸朝店里大喊:“柱子!快,推板车出来,把我车开来。哎算了我来吧你不知道钥匙在哪.......”
好一阵兵荒马乱,把杨伦这大块头搬上车。老周开车,俩人坐在后座,也不敢躺着放,就让杨伦脸朝下趴在贺长青腿缝里。
贺长青都不敢碰他后背上的疮痍,只敢给杨伦擦擦不要紧地方的脏,偶尔摸摸脖根的脉。
那根筋越跳越慢,越跳越慢,贺长青冷汗越出越多,越出越多。
急得他一个劲催老周。
“开快点儿吧!”
可老周说了点什么,除了擂鼓一样的心跳,他其实也啥都听不着。
等终于拿担架给抬进县里的诊所,贺长青让隔在帘子外头,怔怔地看着腿上,手上,泥泞和污血染乱的颜色,整个世界都是嗡嗡声,护士喊他去收拾也没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看见帘子一分,一只大手探出来,冲他招了招。
贺长青快步走上去,握住了一片温热。
好在,好在。
他眼眶终于一酸,交握的画面模糊一片。
这一生与谁携手,与谁相拥,与谁细数平生,都不再荒芜。
愿长风有信,能与日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