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不容易小说在那里看?纯爱小说《美人不容易》由作者张听劝倾心创作,主人公是陆辰赵珩,美人不容易小说主要讲述了:似乎对陆辰来说,在兜兜转转之后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和面前这个人在一起。

《美人不容易》精选:
“定是洛阳士族的公子吧?”“不对,我看着啊,像是将门之后。”几人七嘴八舌的议了半天,齐齐看向颜知,等着一个正确答案。
“我没问。”颜知苦笑,手里布菜的活计不停,“就是问了我也不懂啊。”
他出身不比这些世家公子,哪里知道什么侯府什么士族的。
“那你倒是问了什么?”“知道他年纪吗?”“家中可有在朝为官的?”
颜知并不是背后传人是非的性子,况且也确实是一知半解,便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光顾着给车夫指路了。”
几人齐齐哀叹。
“不过。”其中一人道,“那个小少爷定是来头不小。”
能来这书院求学的,好像就没有一个是来头小的。颜知心想。
“江先生前几日刚接到来信,便让人将南边那间最大的卧房收拾了出来,要知道,那可是江永师兄以前的房间。”
江永师兄是江先生的独子,科考中举后便在雍城留任,很少回咸阳,尽管如此,最南边的卧房江先生还是一直为他留着,如今却收拾了出来让新来的那个小少爷住了进去,难怪大家会觉得稀奇。
“是啊。”另一人也附和,“且书院里都是二人住一间房,那个小少爷却是独居一间。”
“不过话说回来,他若真是家世显赫,怎么连个书童都没有带?”
颜知还是第一次看这群养尊处优的少爷公子哥你一句我一句的猜测着别人的身份地位有多高,不免觉得有趣,于是布完了菜,也没怎么参与讨论,只是在旁安静听着。
不一会儿,从晚枫堂过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各自入座准备用午膳。书院学风蔚然,恪守食不言寝不语,几人便也只好闭了嘴。
此时,后厨的李厨子走到大堂门口,朝颜知比了比手势,示意他过去,然后交给他一个食盒:“给新来的岑小公子送过去,江先生嘱咐的。”
这一下,颜知是真的有些吃惊了。在卧房独自用餐?自他来学院至今,江先生还从未开过此等先例。
不过吃惊归吃惊,他还是马上应承下来,并立刻提着那食盒朝学子们起居的栖梧院送去。
经过大堂时,被那几个同龄学兄瞧见了他手里的食盒,一个个也都是满脸惊讶,对着他疯狂挤眉弄眼。
颜知忍俊不禁。
他提着食盒来到栖梧院,找到江永师兄原来的房间,却有些不确定人是否在此,便轻轻敲了敲房门,试探着唤了声:“岑小公子?”
房门很快打开,开门的岑玉行认出他来:“是你。”
“江先生派我来给你送饭。”颜知把手里的食盒递了过去,岑玉行却没接,只是掀开盖子瞧了一眼,然后又盖了回去,盯着他看。
颜知见状,料想对方八成是在家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伺候惯了。怕对方尴尬,他没有说破,而是径直进屋将食盒摆放在卧房中央的桌子上,一一取出里面的饭菜:“你用完了放着就好,一会儿我再来收。”
“你吃过了么?”岑玉行在他身后问。
“还没有。”
“那坐下一起。”
没想到这娇生惯养的小少爷人还挺和善,颜知虽有些稀奇,却还是微笑着回绝了好意:“不用了,我还要去后院帮会儿忙。”
“……”岑玉行好像没料到会被拒绝,一时沉默。
但凡颜知听得仔细些,便能听出方才那句坐下一起吃,并不是同他商量的口气。
“那,你慢用。我一会儿再过来。”说罢,颜知便留下食盒和饭菜离开了岑玉行的房间。
颜知通常一般等半个时辰后学生们午睡时,才跟书童和帮厨们一块用餐。见时间还早,便去后院打了水,做一些浆洗的活,直到半个时辰差不多过去,才重新去往后厨,领了饭菜,坐在天井里一张小凳子上吃。
今日的例汤里有小块的鱼糜,颜知留了半份汤,又丢进去一小口饭,正搅和着,“嗷呜”一声,一道黑影从屋檐落下,玄墨儿似有灵性,也不上手扒拉抢食,只蜷着身子坐在一旁等候。
颜知将汤水倒进它的小碗,玄墨儿这才起身,走到碗边低下头,小口的舔食起来。
见猫儿吃食时那副有趣中透着文雅的模样,颜知忍不住露出一丝笑容,这时,忽然一片阴影落到了他的背后,他急忙回头,便看见岑玉行站在他的背后。
“岑小公子?你怎么过来了?”颜知低头,看见对方手里拎着的食盒,明白了对方的来意,“用完餐了?”
他本打算吃完饭便去收,实没想到这小少爷会亲自收拾了送过来。
岑玉行举了举手里的食盒:“这个,就放在这里吗?”
“嗯,交给我就好。”颜知将食盒接过,放下手里的食物,小跑着进了后厨。
颜知回来的时候,岑玉行还未离去,正蹲在那歪着头饶有兴致地看着玄墨儿吃食。他长相俊秀,面容恬静,眼神里透着几分少年的天真,看着很是喜人,只是好像不怎么爱笑。
“你要不要去午睡一会儿?离下午的讲学还要两刻钟呢。”颜知上前善意地提醒道。
“不急。今日刚到,江先生让我四处转转,认认人。”岑玉行说着话,却头也不抬,一直盯着猫儿看,“你来这书院很久了吧?”
“我十四岁来此,已四年有余。”
“你既做勤杂,又与学生一同听学,对这里的人想必都很熟悉了?晚饭前,你就带我认认路,顺便介绍介绍吧。”
“……下午?”颜知有些迟疑,且不说下午的讲学,晚膳前后厨若找不到他,怕是要被扣工钱。江先生为了让他听学,已免了他许多杂务,他深知受恩于先生,不可再得寸进尺,玩忽职守。
岑玉行像是看出他的顾虑,道:“江先生那边,我会去说,不用担心。”
颜知心里盘算了一下,青麓书院不大,学生也不过十几人,粗略介绍一下应该也用不了多久,这才点头答应。
一路上,岑玉行一边观察四周,一边抛出问题。只是有些问题细致的叫人心生困惑,他问了学生有几人,分别来自何处,又问了书童,勤杂,采买,护院,马夫,各有多少人,甚至还问了各个的日程和起居习惯。
一个四体不勤的小少爷竟然会关心这些,颜知虽觉得奇怪,但也尽量一一作答。
不消一会儿,未时的钟声敲响,颜知不自觉地朝晚枫堂的方向看了看。
“那是?”
“晚枫堂的钟,江先生马上要开始讲学了。”
岑玉行似乎看出他的心思,问:“你想去听?”
颜知点点头道:“我家中贫寒,听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想了想,又道,“不如,我们一起过去吧?其实去听学也能熟悉人。不用担心,师兄们都很和善,待我这样的人尚且不分里外,更从不排挤新来的师兄弟。”
“不分里外,你却坐在后厨吃饭?”这还是岑玉行第一次露出丝浅笑,却是略带讥讽之意。
颜知被他一句话臊红了脸,尽管他一直清楚自己在书院里身份尴尬,不上不下,只是从来无人去戳破他的窘境。
“罢了,想去你去便是。我自己再随便逛逛。”
颜知不是个钻牛角尖的人,一下子便从刚才的窘迫情绪里恢复了过来,惊讶地问:“可以吗?”
见岑玉行点了头,他连声致歉,然后便朝着晚枫堂一路小跑了过去。
这天短暂的相处,让颜知错以为岑玉行是一个有些怯生的少年,却不料没过几日,他便已经与同门师兄们熟识起来,也不再独自在房里用膳了。
江先生将他安排在晚枫堂最靠前的长案上,每当讲学结束,那张书案边总是围满了人。对于同门的热情,岑玉行一贯带着得体的微笑应对,只是每当被问及籍贯,家世之类的问题,他便推说不便透露。
因他回绝的直白,再加上江先生特殊的对待,众人也不是很敢追问。慢慢的,那众说纷纭的猜测也消失了,大家的口径变得统一起来,都说岑玉行的身份定是岑皇后的娘家人,是天子的外戚。
坐在角落的颜知只在戏曲里听过这种身份,即便隔着人群远远看着,也能感受到岑玉行举手投足间,那份从骨子里透出的贵胄气质。
不愧为皇亲国戚。
就这么过去了几个月,一天夜里,颜知清扫完了后厨院子,正洗手准备回家,忽然听见栖梧院传来一阵骚动。
青麓书院一向静雅,极少出现这样大的动静。
颜知担心出事,慌忙擦了手往栖梧院赶了过去。
一路上便嗅到一丝烟熏火燎的气味,颜知心道不好,莫不是走水?脚步越发加快。
穿过月洞门的瞬间,眼前的一幕将他惊呆了。
只见院子周围乌泱泱的站着手忙脚乱的同门师兄,一个个手里都提着桶,拿着盆。
一团火球,在院中上蹿下跳,一面发出凄厉的嚎叫,一面躲闪着靠近的人。
“玄墨儿!”大脑一片空白的颜知喊出声来。
今天午膳时便不见玄墨儿踪影,颜知喊了许久也没见它来吃食,不过以前它也会山下玩耍,跟行人乞食,所以颜知也并未多想。
可如今,透过那团火球,他分明看见了那双熟悉的金色的眼睛。
颜知立刻将身上的外袍脱下,朝着火球窜逃的方向疾步奔去,然后飞身一扑,将那火球罩进了外袍,死死的摁在身下。
因着惯性,他连人带猫跌出去半米,扬起一地灰尘,手臂也擦破,却顾不得,只是大喊:“水!!”
一桶救命的水当即迎头泼了下来,火舌烧穿了他的外套,遇了水也不平息,直至更多的水,一桶接着一桶,一盆接着一盆的倒下,火苗才彻底熄灭,烧破了洞的外套里冒出一股焦臭味来。
“颜知师弟!”
在旁的同门师兄们这才反应过来,慌忙拉开颜知,检查他的伤势。颜知此刻好不狼狈,浑身湿透,发髻也散了,脖子烫出了血泡,手臂也擦破了一大片,不停的冒着血珠子。可他再狼狈,也比不得那件外袍下的活物凄惨。
玄墨儿的眼耳口鼻都已几乎没了形状,那身油光铮亮的黑色毛发也烧了个干净,它像是瘦了一圈,身上焦黑一块灰白一块的,死了一样躺在地上,只是肚子还一息一息的喘着气。
颜知与在场所有人一样,瞬间红了眼眶,不忍再看。
唯有岑玉行面无表情站在人群后边的回廊上,双眼紧盯着那仍在喘息的小小身躯。
-------------------------------------
学生们小心翼翼地把玄墨儿放在一个铺了棉麻布的竹篮子里,找来后院的马夫过来帮忙。
马夫只看了一眼,就说:“不成了。”
就算已大概有了猜测,可真听到这一句,所有人还是心有戚戚。
“怎么会这样。”
“早上还好好的。”
“究竟是哪个禽兽干的?”
只有年纪最长的卢师兄安慰着围在竹篮边的师弟们:“要是玄墨儿能挨过今晚,明天一早,医馆开门,我去抓些药,也许也还有救。”
众人纷纷附和点头,只有颜知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拾起地上烧毁且湿透的外袍,安静地准备离开。
因为他很清楚,就算再不愿面对,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玄墨儿是活不了了。
“颜知师弟,你受了伤,今夜不要下山了。”卢师兄道,“就住在我屋里吧,我那还有些伤药。”
“……不了。我身上的伤不碍事。”
颜知每日早上上山,晚上下山,并不是因为书院里没有给杂役的住所,而是因为家中还有母亲在等候。父亲过世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实在不忍留母亲一人在山下独自生活。
他谢绝了众人的挽留,向众师兄道别,然后便从来时的月洞门出去了。
回到家中,颜知那狼狈的样子吓了母亲林氏一跳,他怕母亲受惊,只是轻描淡写的讲了讲书院里发生的事,说自己救火时不小心跌了一跤,而后便去后院打水擦洗身体去了。
擦洗泥污容易,可要取出手臂伤口下尖利的石子实在疼痛,颜知借着月色,清理一会儿歇一会儿,最后又简单包扎了一下手臂,弄了大半个时辰才从后院回来。
“来。知儿,试试合不合身。”
一进门,母亲林氏便将一件灰蓝色的外袍罩到了他身上。
颜知将粗略包扎的手臂穿进袖子,然后低着头,盯着那灰蓝色的布料出神的看。
他记得这件外袍,是他过世的父亲留下的,母亲大概是怕他明日没有外袍会受凉,临时起意将它剪裁了一部分,改小了些。
颜知十二岁便没了父亲,正是最记事的年纪,他清清楚楚的记得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
那时,大夫也说了和今日马夫所说的话。
“不成了。”
然而父亲仍在强撑,邻居和远亲也帮忙找来不少古法偏方,母亲则日日强颜欢笑。
大家都告诉年幼的他,会好的,还有希望。
他信以为真,可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不过一个多月还是走了。
那时起他就知道,谎言和自我安慰不能阻止任何事,该来的总会来。
林氏见儿子走神,关切地握了儿子的手,看着那往外渗血的手臂,心疼道:“还疼吗?”
“已不疼了。”
“等明天医馆开门……”
“娘,用不着。只是皮外伤,过几天就自己好了。”颜知将手臂收回了袖子,他知道家里拮据,自父亲过世之后,母亲没日没夜的织布绣花,眼睛都快做盲了,也只是勉强维持家中生计。
几年前有一回,他下山时淋了雨,当夜便突然高烧不退,为了给他看病,母亲把嫁妆都拿去典当了,头发也愁白了大半。
如何能病,如何敢病。
颜知甚至想,如果早知道救不回玄墨儿,当时他便不该如此冲动以至于负伤。
一时疼痛事小,让家中破费、让母亲忧虑事大。
“放心吧,娘。孩儿身体好着呢。”
“还是小心为好……”林氏喟叹了一声,她又如何不知儿子在想什么,只是家里确实也没有那请大夫的银钱,她只能向现实低头,淡淡道,“那娘去给你煮碗鸡蛋糖水,喝了暖暖和和的睡上一觉,便不会受凉。”
“好。”
这天夜里,一贯睡眠很沉的颜知睡得不怎么踏实,似乎总有一团火在梦里攒动,从火里面隐隐约约透出一双金色的猫儿眼。
半夜,他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屋外传来断断续续的人声,他撑起身子往房门方向看去,发现门扉半掩着,月光下依稀有两个人影在说话。
“他大伯,您就再宽限几日,我手头这几个样子就要做好了……”
林氏的声音被打断。
“宽限几日?我便是宽限几年,你就能填上了?”
“到了月底,知儿的工钱也会结下来。到时候……”
“弟媳,两年了!你年年就只还利息!?当初侄儿重病,不是看在你们母子俩可怜,又怕断了我二弟的香火,我就不该借出这二十两银子!”
“他大伯,你就看在他爹的份上……”林氏苦苦哀求。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移了话题,“侄儿还在那个什么劳什子书院打杂么?就这点工钱,怎么还非吊死在那了?我早跟你说过,侄儿毕竟上过几年学,识得几个字,去医馆做个学徒,等过几年当上了掌柜的,那银钱不比在书院做杂役多得多?”
“大伯,知儿在书院打杂也是为了求学。您知道,知儿从小就聪慧,连青麓书院的江先生都夸他是有天分的。”
“你省省吧!县里这么多读书人,四年又四年的科考,有几个中举的?你再看看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还指望着祖坟冒烟,一步登天不成?”
“大伯,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看在过世的知儿他爹的份上……”
“……”听着门外来来回回的车轱辘话反反复复的说,颜知有为母亲出头的冲动,却又压了下来,慢慢地躺了回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拿不出钱来,又如何为母亲出这头,若激怒了对方,只是让母亲将来更加难做。
他只能攥着被子,紧闭着眼,不去想象向来温柔软弱的母亲被人为难的模样。
方才见玄墨儿惨状都不曾流下的泪水,此刻却在少年的眼眶里蓄不住了。
世道艰辛,众生皆苦。寻常人的生计,怎么就这么难呢……
干完这个月,便依大伯说的,去医馆做学徒吧。他想。
+++
自从打定了离开书院的主意,颜知便愈发卖力的干活了。便是先生讲学的时间,他也不再去晚枫堂听学,瘦小的身影总在后厨,后院,马房忙活。
他打心里感激这几年来江先生的赏识,也铭记同门师兄们的帮助,可人各有命,他颜知的命和同门师兄们天差地别,是他认清的太晚。
青麓书院给他的那些善意,他无以为报,只能在最后的时间里多做一些粗活重活当做偿还。
一日傍晚,他在后厨的灶台后分拣柴火,忽然听见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他本以为是李厨子,也没多想,可来人却在门口停了一下,似乎是对这里不熟。
颜知这才探头看了一眼,然后便吃了一惊。
竟是岑玉行。
他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还来不及细想,却见他径直朝着储油的陶器走了过去,颜知瞪大了双眼也不敢相信,对方顺走了一大罐子的豆油后就悄悄离开了。
岑玉行要豆油何用?
颜知忽然感到不寒而栗。
近日,山下的人家频频丢了猫儿狗儿,等到找到的时候,那些猫儿狗儿都像玄墨儿一样,被人给点了火,烧死了。
须知若不是给猫儿狗儿的毛发浸了油,是很难用火将猫狗活活烧死的。因此县里都在议论,这些都是油铺那游手好闲的大少爷干的。
可议论归议论,没有真凭实据,再义愤填膺,人们也拿那二世祖毫无办法。
但此时颜知才忽然意识到,书院后厨的油总是一次性采买许多,也没有人负责每日清点,就算少了一罐两罐,恐怕也不会有人发觉。
而岑玉行入学第一天,就曾打听过后厨人员的日程安排,若不是自己最近突然发了疯的干活,今日他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取走那油罐子。
今日是如此,那之前呢?
难道是他……
颜知不敢细想下去。
他放下手中的细柴禾,离开后厨,找到刚走不远的那个背影,悄悄的跟了上去。
岑玉行不急不缓,径直从后厨院子的偏门走了出去,从一条幽静小道离开了书院。
明明也才来书院没多久,他却似乎对复杂的山路很熟悉。
他身形出了奇的灵巧,崎岖山路完全难不倒他,而且,明明两侧杂草灌木枝繁叶茂,当他经过时,却仿佛连片叶子都不会动。
颜知好几回都差点跟丢,好在他对山上的岔路相当熟悉,最终还是在一棵歪脖子树下找到了岑玉行的身影。
只见他半蹲在树下,手里摆弄着一个硕大的麻布袋,麻布袋里显然装着什么活物,在地上不停的蛄蛹着。
岑玉行从怀里掏出一柄细长的短剑,割开了麻布袋口的系绳,当看清里面装的东西时,颜知发现,哪怕是自己最坏的揣测,也远远不及真相的万分之一恐怖。
那麻布袋里装的,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人双手双脚都被捆着,嘴也被布条死死封着,发不出太大的声响,他年纪看上去有近三十岁,身形高大,可岑玉行将他从麻袋里弄出来却似乎毫不费力。
岑玉行用一根粗麻绳勒住他的脖子,将他堪堪脚尖着地的吊在歪脖子树上,然后割开了他嘴上的布条。
那人立刻踮起脚,抻着脖子大喊:“你,你是什么人,究、究竟想干什么!……救命啊——救——!”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岑玉行手里的刀抵上了他的喉咙。
“小点声,可以吗?”
那人急忙点头,他慌乱的眼神四下乱瞟,想找到什么能脱困的办法,却看到了一旁的油罐子,顿时脸色发青起来,把刚刚答应的事也瞬间抛到了脑后。
“我赔!……我赔你!是狗吗?还是猫儿?我赔你就是了!你别——你别——!”
“嘘——”
岑玉行凑近了他,捂着他的嘴,手里的刀移到了他的右胸下两寸的位置,毫不犹豫的刺了进去。
“唔!!!!”哪怕是被捂着嘴,那人仍是发出了无比凄厉的惨叫,双眼倒翻了过去,而岑玉行并未停手,将刀子抽出,又对着他左胸下两寸的位置刺了进去。
颜知离得远,本未看清他做了什么,只看那人挣扎的厉害,过了一会儿,才看到鲜血顺着那人的身体淌下,洇湿了脚下的泥土。
他顿时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那两刀并不会立刻致死,却刺破了肺,哪怕不再被捂着嘴,男人已发不出洪亮的声音了,只能气短地发出一声声告饶:“饶……饶命……我……银子……”
岑玉行撇下他,甩了甩短刀上的血,收回了袖中。
“不是狗。”他弯腰拾起一旁的油罐子,走到那男人跟前,打开罐子从男人的头顶浇了下去,“也不是猫儿。”
他倒的不徐不缓,就像怕浪费了一滴豆油似的,直到把罐底的几滴都尽数滴进男人的头发缝,才随手将罐子丢到一旁:“它叫玄墨儿。”
“饶命……我……我……错了……饶命……”
事情到了这一步,对方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男人满眼都是绝望,哭得涕泗横流,上气不接下气,却仍不住的求饶。
但岑玉行就像听不见男人的声音似的,退开了几步,从怀中取出一个火折子,甩了几下,丢到了男人的脑袋上。
那瞬间,窜起的火光映进了颜知的眸子。
跳动的火焰中,男人发出凄厉非人的嘶喊,最先燃起的是浸了油的头发,烧断的发丝掉落下来,又点燃了男人身上滴了豆油的衣物,很快,原本男人的形状便被吞没在了火焰之中。
等火焰烧断了男人脖子上的粗麻绳时,“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的已是一具不会动弹的尸体,而尸体上那熊熊大火仍在燃烧。
岑玉行就像在看一场烟花表演似的负手立在一旁,表情平静,悠然自得,直到火苗渐息,才拾起一旁的油罐子,沿着来时的路离开。
他身上干干净净,滴血未沾,连烟火味都仿佛被那淡淡的熏香压了下去。
躲在草丛中的颜知死死的捂着自己的嘴,不知过了多久,才心有余悸的从草堆里爬了出来。
空气里烧焦了肉的味道令人作呕,他刚直起身,便又蹲了回去,跪在地上干呕起来。
报官!报官!
心里的这个念头,支撑着他艰难爬起身来,疯了似的往山下跑。可路上一回想到刚才的事,双腿便又一阵发软,导致疾奔中的他一个不稳,身子一歪跌出老远。
手臂上那还未愈合的伤口再次渗出血来,他挣扎了半天,也没能爬起来。
他年岁尚浅,又自小生活在民风淳朴的泾阳县,刚刚发生的事对他而言,实在是太残酷,太出格了。
可与他同龄的岑玉行,却可以做的那样得心应手,平心静气。
绝无可能是第一次。
他忽然想起见到岑玉行的第一天,对方说的来青麓书院的理由。
[做了错事,母亲让我来的。]
本以为岑玉行的意思是来此受罚,如今回想,却更好像是来此避避风头。
颜知甚至不敢去细想,那错事,究竟是什么?
他手上究竟有多少条人命?
自古杀人偿命,他却可以当做无事发生一般,在家人的安排下逃脱罪责,逍遥法外。
难道就因为……他是岑皇后的娘家人,天子的外戚,便可以如此无法无天吗?
颜知撑在泥里的双手忽然间握紧了,粗粝的泥沙刺痛了他的掌心,少年的眼神在这一刻变了。
这世道就没有公允过。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是一句话本里的迂腐话。
现实是——皇亲国戚可以欺市井百姓,油铺的少爷可以欺猫儿狗儿,正如伯父可以欺他母子软弱,在父亲过世后,侵吞他家的田产。
贫弱者注定长埋黄土,无冤可诉!
这一刻,他决定了,从此不再受欺哄。
他不愿再做贫弱的那一方,与其安守本分,期冀于上位者赏的公允,不如豁出去,在高高在上的权贵身上啃下一块肉来。
想到这一层,颜知忽然静了下来,报官的念头也不复存在,哪怕内心深处仍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也将之硬生生压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以思考接下来的对策。
***
颜知回到书院时,天色已暗,李厨子正四处找他。
李厨子本想教训他地未扫水未打,见他脸色惨白,一头冷汗,又不忍心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在林子里摔了一跤。”颜知道。
“你去林子里干嘛?也不怕遇到大虫?”李厨子闻言将他上下打量一番,见他受伤的手臂渗出血来,忙道,“罢了罢了,这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
颜知想了想,道:“李叔,我摔伤了腿,今夜没法回去了。能不能在您房间借宿一宿。”
“可以啊。”李厨子爽快道,“这你就别管了,快去休息吧。”
颜知谢过李叔,然后径直去了栖梧院,他走到长廊的尽头,停在了最南边的卧房门口。
卧房里透出昏黄的光,显然,人在。
颜知站在门外许久,才下定那破釜沉舟的决心,叩响了跟前的房门。
他没说话,里面的人也没问,过了一会儿,岑玉行便将房门打开了。
此时的岑玉行已经换了一身就寝的衣裳,白色的缎子亮的晃眼,映得他愈发的两腮似雪,而门外的颜知,身上、脸上都满是泥污、血污,隔着一道门的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见来人是颜知,岑玉行好像并不奇怪,尽管这些时日两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交集。
“我有话要和你说。”颜知道。
岑玉行略一思忖,道:“要进来吗?”说完,在门前让开一步。
颜知知道这一步进去之后生死难料,可也并未犹豫多久,大步迈了进去。
等他进屋,岑玉行便将房门紧紧的闭合上了,然后好整以暇的倚在门上,像是故意堵死了唯一的出口:“说罢,什么事?”
“我看见了。”颜知不说一句废话,开门见山道,“你杀了油铺家的大少爷。”
“我看见了。”颜知不说一句废话,开门见山道,“你杀了油铺家的大少爷。”
“真的?”岑玉行不仅完全不慌张,还似乎觉得有趣,“那你怎么不去报官?”
“这人……本也该死。”
颜知这话倒不是违心的,书院里的人就没有一个不疼玄墨儿,更何况,那二世祖不止一次残害生灵,着实可恶至极。
听他这么说,岑玉行的眼睛里第一次闪过一丝意外的神色。
“我来是想给你一个机会。”颜知没有余力观察对方的表情,自顾自道,“只要你能满足我的条件。我就不会去报官,我说到做到。”
“……”岑玉行眨了眨眼,微微回神后,问:“什么条件?你说说看。”
“我要银子。”颜知一字一句道,“二十两银子。”
话音刚落,他便看见岑玉行眯起了眼,脸上带着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问:“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是又如何。你有的选吗?”颜知说道,“这个时间栖梧院里全是人。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便大喊。”
“是吗?我还真有点想听听看你大喊呢。”
颜知虽然感到害怕,眼神却丝毫没有动摇,在迈入这扇门前,他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为了前程,他愿意去赌。
“对你而言,这只是一笔小钱吧?只要拿到那二十两,我便将今天看到的事永远埋在心里。”
听他说完这些,岑玉行垂着眼,好像在思考,过了一会儿方开口,语气爽快道:“没问题。”
颜知瞬间仿佛卸了全部力气,他着实也没料到事情会进展的如此顺利。
“只不过——”
“……?”
颜知立刻恢复了戒备,他不知道自己这副样子,在对方看来就像一只警觉的兔子。
“我出门时,母亲怕我闯祸,并没有给我现银。问题倒是不大,我可以拿些物件去典当,要不这样吧……”岑玉行像在商量出游踏青一样,语气轻快地问,“你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同样的时间,你再来一趟,到时候,我一定准备好你要的东西。”
“…………”颜知方才完全没考虑过这样的展开,一时拿不定主意。
三天后?再来一次?
“不是你说的吗,这个时间的栖梧院里全是人。你想大喊,三天后也可以大喊,没什么问题吧?”
颜知一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只能强装镇定:“好,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谈成了条件,岑玉行便很大方的打开了房门。
颜知走出那间仿佛龙潭虎穴的卧房,脚底仿佛脚踩着棉花,一时竟不知方才那一切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哦,忘了提醒你一件事。”岑玉行忽然从背后凑近,在他耳边道,“这几天最好不要一个人待着哦,要是落单的时候被我杀掉的话,这二十两你可就拿不到了。”
颜知惊惧之下猛回头,岑玉行却已先行一步将房门关上了。
***
颜知生活虽然艰苦,但人生过去的年岁里,即便再苦再累,他也从未过过如此心惊胆战的日子。
他怕牵连家中柔弱的母亲,便决定这几日都在书院里待着,直到拿到岑玉行的二十两为止。可即便他如此打算,做事时,还是难免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
而另一边,岑玉行却仿佛无事发生一般,照旧和同门聊天,吃饭,听先生讲学,完全不像是个正在受胁迫的人。
同时,县衙的火差已发现了山上的尸体,县里派了几个捕快来青麓书院例行问话,颜知有些忐忑地推说不知,捕快们也未多问,毕竟青麓书院的名号响亮,且油铺那位作恶多端结怨过不少人,这群年轻的世家子弟显而易见的并不是被怀疑的首要对象。
颜知发现,哪怕是自己和官差说话的时候,岑玉行也不曾露怯,依旧在人群中谈笑风生。
直到第三天的正午,颜知正在大堂布菜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头看见是岑玉行,他险些打翻了手里的饭桶,瞬间退开一米远并四下找人。
“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岑玉行道,“我来是告诉你一声,我和江先生告了假,准备今天就下山,去一趟县里。”
“……”颜知稳了稳心神,“这是你的事。我只关心明天夜里我要拿到那二十两。”
“放心吧。”岑玉行还从未笑得如此灿烂过,“那我走啦?”
“……”
颜知没有回话,他实在不懂对方为什么还要特地来跟自己知会一声,只是神情凝重的目送着那人离开了大堂。
岑玉行这一走,便三四个时辰没有回来。若只是典当物件,何须这么久?颜知十分不安,待到深夜,想去栖梧院看看,又想到他那夜的警告,不敢单独过去。
忐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来干活时,他才在大堂见到岑玉行和师兄们坐在一起用早膳,也不知昨夜何时回来的。
就这么魂不守舍的挨到了深夜,终于是等到了约定的时间,颜知告诉李厨子自己要去一趟栖梧院,然后便去赴三日前定下的约。
“你来了。”开门的岑玉行看起来相当的期待,“进来吧,我都为你准备好了。”
颜知沉默走进那房间,看见屏风旁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精美的小匣子,想来那便是自己要的东西了。果然,岑玉行关上房门后,将那匣子拿起,朝他递了过来。
颜知正准备伸手去接,却忽然听见他问:“有了这个,你便不用离开书院了吧?”
“……什么?”颜知的动作顿了一顿。
“前几日……”岑玉行道,“我和师兄们打听了一下你的事。”
“本来我就觉得奇怪,你写的一手好字,文章也作的极好,一定是从小便开始读书习字的。”
“于是随便打听了一下,果然,你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还算是个富农,那时,家里供你上私塾绰绰有余。”
“我还听说,你父亲过世之后,伯父家要求重新分家,将原本属于你父亲的田产都占为己有了。真是个坏伯父呢,摆明了欺负你们孤儿寡母嘛。”
可能是因为过于紧张了,颜知只觉得岑玉行每一句话都令人毛骨悚然,哪怕语气和内容都很正常。
“你打听这些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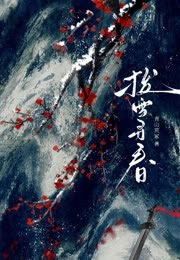




![师徒文学,但师尊在上[穿书]小说](https://img.gljjx.kouwz.com/storage/20250604/UiDKbTjgifVkrrEAlmEZ.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