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为许长风萧玄小说叫《万年春》,作者:泽正,小说剧情精彩,吸引眼球,实力推荐大家观看。万年春主要讲述了:萧玄没有把许长风当老师,在很小的他心里,也想着有一天可以和许长风在一起。

《万年春泽正》精选:
熹平十一年,宸帝溘然崩殂。
后记曰:“帝在位十年,素以黎民为先,励精图治,举贤用能,是以河晏海清,民乐国强。其时,平倭奴,攘疆土,功绩赫赫,非数言以述。
然,天不遂愿。彼年,帝三十有一,突遭恶疾,仙登于天。百姓闻之,莫不痛绝悲嚎。以帝殚力于国事,过后宫而不入,致无一子嗣。遂,传位于昭王。”
皇皇盛世,宸帝驾崩一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仓虞村,此地也是许长风十年前向先帝辞官,归隐之所。
那年,许长风来到此处后,就在村子里当起了私塾先生。此间地远,距皇城千里迢迢。
“夫子夫子,您可还好?”几个孩童见先生听了这个消息后,倏然愣在了原地,脸色更是大变。心下只当他也是如家中阿母一般,觉得皇帝崩逝,天道不公,心中难免悲痛。其中一个便抬头扯了扯他的衣袖,略带关切地询问先生。
“无碍,今日的课先不上了。”
许长风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心口,好疼啊……脸上已然没了半分血色,浑身都在止不住地发颤。
他强行稳住了身形,嘴里含糊地说道:“你们且先回去罢。”
既然先生这样说了,聚在一起的稚子们便也散了去,各自回家了。
许长风颤颤地扶着门框,脸色发白地抬眼看了看屋外,扶光正好,尤为明媚,他抬步踉跄地就朝外走去。
“……”
“陛下,这一切肯定都是假的,对不对?”
“你说过,不论山高水远,天涯海角,你都会来寻我的,君无戏言,断然不可不作数啊……”许长风捂住了刺痛的心口,视线渐而被泪水模糊了。
“不……怎么可能?你从小百病不侵,在雪地胡闹数日都生龙活虎,怎么可能走在我前面?不是病逝,那是谁害你?苏家旧部?还是皇族中人?!”他强行稳住了身子,方不至于让自己倒下去。
“对……都是讹传……我要亲自回京城看看……不,先去衙门……”许长风在心里一遍遍地否认着这个天下昭然的事实,加快了步子。
“噗!”没走几步,他却顿感喉间涌上了一股浓重的腥甜,不由地顿了顿步子。下一刻,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恍惚之际,他的面前甚至扬起了一片血雾,月白色的前襟顷刻便被鲜血染红。随即重心不稳地晃了晃身子,两眼一黑,颓然地向后倒去。
“长风!”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玄色稳稳地接住了倒下去的许长风。
“长风,你醒醒……”萧玄心疼地呼唤着怀中双眸紧闭,脸上血色尽褪的人,抬手慌乱地替他揩去了嘴角还在渗出的血丝,没再多想,他抄起了对方的膝弯,立马将人抱回了屋内。
萧玄方才已经找人为许长风诊治过了,好在只是郁火攻心,以致气血上涌,所幸并未伤及肺腑,吐了血反到会令他畅达不少。
直至薄暮时分,许长风才悠悠转醒。
萧玄一直守在许长风的床榻旁,他把许长风的手始终握在了手心,方才对方手指微动,萧玄便知他将要苏醒。这会儿,看着对方缓缓睁开了双眼,顿时喜不自胜起来:“长风,身体感觉如何?”
“陛下?臣怕是在做梦……”许长风借着对方伸过来的的手,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五官深邃,气宇轩昂的男子,许长风摇了摇头,苦笑了声,再度闭上了双眸,将头倚靠在了床头。
“臣梦见过陛下无数次了,多少次午夜梦回,留在臣床前的,不过空余一方冰冷的月光。”
“罢了罢了,至少臣还能在梦里同陛下说说话,也是好的……”许长风只当身边这人也不过是自己的梦,嘶哑着声音喃喃地自语着。
“唔……”萧玄却是再也忍不住了,眸光深了深,抬手托住了他的后颈,俯身下去用唇堵住了对方的后话。
许长风这副不自信的模样,看得他只想把对方搂入怀里,用行动狠狠地告诉他,自己不是梦,明明此刻就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眼前。
许长风被吻得差点喘不上气,直至几乎瘫倒在对方的怀里,那人才堪堪拉开了和他的距离。分开之际,两人之间甚至还带出条绵长透亮的水泽。
看着许长风微微偏开脸,有些急促地大口呼吸着,萧玄勾了勾嘴角,捏住了对方的下颚,将人的脸又扳了过来,眸子里闪烁着晦暗不明的情绪:“许太傅,你可真是让朕好找啊……”
“陛下,臣……臣何曾让陛下难找了?”许长风这才相信,眼前的人就是自己心心念念要见之人,激动地说起话来都开始磕磕绊绊。
“……”
“陛下,您这出金蝉脱壳的戏码,当真是演得极好。”许长风看着眼前这人一脸眉欢眼笑的模样,忽地想到对方撒下的那个弥天大谎,心里就来了火,蹙了蹙眉头,颇为恼怒地指责起对方来。
萧玄闻言,倒也不恼,伸手撩起了许长风披散开来的一缕青丝,放在唇边吻了吻,深深地望着他,笑问:“不知太傅,可曾还记得与朕的十年之约?”
溺在萧玄满是深情的眸子中,许长风的脸颊开始有些发烫,随即微微瞥开了脸,清了清嗓子说道:“陛下还是别叫我太傅为好,臣早就辞官了。”
“好,那还是唤你长风罢。”萧玄看着对方泛红的耳垂,心里欢喜得不行,轻笑着开了口。
“……”自己的名字,对方素来是想唤便唤的,还多问一句做甚。
许长风怎会不记得,那晚萧玄借着商议要事之名,将他召去了养心殿。期间,却是一杯又一杯地劝他喝酒。他酒量本就不行,仅是三杯入喉,他就醉得不省人事。怎知那厮竟然乘人之危,把他抱去了龙床,拉着他共赴巫山。
翌日清晨,许长风醒来便发现自己躺在对方的怀里,那人正用手支着脑袋,深情款款地看着他,还厚着脸皮笑问:“长风,昨夜可还舒服?”
许长风当即被气得不行,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大逆不道!欺师灭祖!”可那人的脸皮似乎是铁铸的一般,望着许长风的动作,他只是勾唇一笑,随即捉过了对方的手指,放在唇边狎昵地亲吻着。
待许长风骂得嗓子干了,他还不徐不急地递过来一杯水,让他喝完了接着骂。
“太傅又不是不知,这世间礼数清规,朕向来是不屑睥睨的。”
“朕认的只有,心之所向。”看着许长风气得睫毛颤抖,眼眶发红,萧玄颇为心疼地将人又摁到了怀里。
“……”
末了,见怀中人逐渐安静下来,萧玄不忘贴着他的耳畔,轻佻着笑道:“太傅俊美无俦,朕十几年前,就想尝尝太傅的味道了……”
“如今看来——”
“朕怕是食髓知味,不知餍足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许长风脸上泛红,气得他就给对方胸前捣了一拳,匆匆穿好了衣物,便扶着腰离开了那人的寝宫。
临走时,恰好碰上那前来送药膏的御前侍卫江青锋。
“太傅大人,今日休沐,这便走了吗?”他笑着挑了挑眉,视线不住地往许长风有意遮掩的脖颈处打量,“不再多留一会儿么?”
不必多想,萧玄定是将这事告诉了他。几人的关系自少时起,便尚且不错,他知晓也无何不妥之处。
但终归还是脸面上有些挂不住,许长风冷哼了句,便头也不回地逃了。
不过,气归气,自己心里却是欢喜的。他的心意又何尝不是如他一般?
当年辛夷树下,花叶簌簌。少年一袭红衣,长身玉立。他于东风中回眸,两两相对之际,对方那双好看的桃花眼里盛满了深情。
彼时,他向自己款步而来,行至身前,微微躬身,温柔地唤了他句:“先生。”
此番初见,便让他惦念了半生。
打那以后,每逢上朝,那人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挑逗自己,甚至平日里遇见他的次数也愈发勤了,若是四下无人之时,他拉着自己就是一番缱绻。
自己试过拿“老师”这个辈分去压他,那人却揽过他的腰,挑着眉头,一脸不羁地笑道:“太傅啊,细细算来,您不过也只是比我年长几个月罢了。”
“所谓‘太傅’之位,不过是虚名一个,真要论起辈分来,朕理应与您兄弟相称的。”
许长风愈发理亏起来,长睫微颤,紧紧咬着下唇,偏开了脸,一言不发起来。
萧玄看着他这副模样,越看越喜欢,便俯身靠近了他,微微喘着粗气,贴近了对方耳旁,声音暗哑:“长风兄,帮帮我……”,随即抓住了他的手,隐隐向下探去。
“陛下……”
又是一番携云挈雨,缱绻旖旎。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他们之间的不伦之恋还是传到了朝堂之上。一时间,对帝王的痛心和对他的辱骂,如洪水猛兽般铺天盖地地袭来,让他们避无可避。
臣子妄加揣测,谣言当今圣上不思朝政,耽于情色,被许长风迷了心窍,咒骂他祸国殃民,不该留在皇城,乃至不配苟活于世。
不乏有古板腐朽的老臣,甚至以死相逼,要挟皇帝将人永久流放到边陲之地去。
是时,萧玄高坐在龙椅上,冷冷地看着底下的臣子置边关军情,疠疾天灾于不顾,却死死地抓着自己与许长风的事大做文章,胡乱编造,传的尽是些子虚乌有之事。个个此时还在吹胡子瞪眼,虚言妄语。
朝堂之上,一派乌烟瘴气。
本是两心相投的情爱,却被这悠悠之口变相扭曲,为世间所不容,当真是荒谬至极。
他眉头蹙得极深,袖袍下的五指似是要将龙椅掰裂。
“陛下,臣有本启奏。”那中书令长子苏见林兀然站了出来。
“怎么是他?”
“他父亲的罪状已是昭然无疑,他不会还想为他父亲开脱吧?”
“陛下念及他爹苏淮是前朝老臣,留了几分皇恩,他可别自己也跟着下狱了……”
见状如此,群臣纷纷观望,窃语不止。
“你!”萧玄本就烦心,现下怒气更甚。
苏见林听出了皇帝的不悦,却直直跪了下去,把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咬牙死谏:“陛下!臣要弹劾许太傅蛊惑帝心、构陷家父!”
眼下时机尚好,他不能白白错付。
一语罢,朝堂复又喧哗。
“此事怎地和许太傅扯上关系了?”
“许太傅素来好手段,只怕是向陛下吹了枕边风呐……”
“若是许相尚在,至于如今局面,不知该如何自处,怎有颜面见先帝?”
“……”
枉口拔舌,句句诛心。
“住嘴!胆敢再加妄论,朕定斩不赦!”天子震怒,一掌重重地拍在了龙椅上,骤然起身,冕冠上的旒珠也因这一动作剧烈摆动,依稀可以看清,玉串后此时是一双透着杀意的寒眸。
他们的君王从未有过这般滔天怒火,一时间,朝堂顿时沉寂下来,群臣皆跪,无人敢言。
“退朝!”着实让人心寒,萧玄眉心成川,不想再去看底下的朝臣,愤愤拂袖,转身离开。
“岂有此理!”子时,萧玄还在批阅奏折,看着看着,骤然蹙起眉头,怒喝了声,旋即把一道折子狠狠扔掷在地。
许长风彼时正在帮他研磨,见状,停了手里的动作,蹲下身子捡起了地上那道折子。
他草草扫了一眼,果是如此,无非又有臣子递了折子上来,辱骂诋毁自己,要他滚出皇城。这样的折子,已经有好几份递到了皇帝这里,他已经看得惯了。
许长风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不过是喜欢上了自己的命定之人罢了,况且,对方也是把自己放在心上的。这世间情爱本就难求,更遑论这般难得的缘分。
他抬眸看向了自己认定的良人,此刻对方正紧闭着双眼,疲惫地揉着眉心。
只一眼,许长风便垂下了眸子,心里揪疼不止。
这段时日,他染了风寒,缘而告了假。
白日里,他听江青锋提起过,那苏淮之子苏见林借机弹劾自己魅惑圣上,排除异己,并扬言他父亲就是被如此陷害入狱的。
执理若非其父与前朝中书令有裙带关系,中书令之位本该是自己的,所以自己对苏淮心存记恨,方才万般构陷……
彼时,许长风只觉着可笑。
苏家现已穷途末路,少年人心性如此,不知轻重,难免禽困覆车。
可眼下势之所趋,便又是另一场局面了。
自己受人忌惮,纵使清白坦荡,心如朗月,也合该被清算出局。
许长风并不畏怕,但他实是不愿连累心上人同自己受罪。
念及萧玄每日都得为此事所累,他心里就难受得很。
现下风波难止,适才连早已辞官归去的起元先生也来找过他,免不了对自己的学生便是一番劝慰。
“孩子,听先生一句劝——寻个机会,离开朝堂吧。”
先生是看着他和萧玄长大的,两人早些年便已有端倪的心思,怎能逃得过先生的法眼。
苏起元曾以为,情爱何如,俩人少时不甚了了,所言知慕少艾,自当匆匆来去,届时都将化作云烟散了。缘而,他便也未加过多管束,怎料,两人如今仍是冒了这天下之大不韪。
可身居庙堂高位,是非曲直,早已成了他人的春秋笔法。口诛笔伐之下,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老师说的那些道理,许长风无一不深谙,可到底还是难舍心中那人。
折子上的后半句,许长风最后强迫自己尽数看完了。
字字句句,犀利扎人。
【册有曰:宸国开国之前的王朝,不乏有毁于君王的昏庸无道。兴土木,课重税,宠男后,灭发妻,致使礼崩乐坏,民不聊生。
陛下,臣死不足惧,惟愿陛下能早日醒悟,稳朝局太平……】
他将手里的折子死死握住,闭了闭眼。
是了,老师说的没错。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任何与历史相似的事物都会勾起朝臣和百姓心中的恐惧。
他或许,不该再自私的。
手头太过用力,以致他的指甲已然开始隐隐泛白。
千秋丹青,吏书陈录,他的陛下都不该被笔诛墨伐,人寰诟病,生生背上那莫须有的罪名。
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许长风睁开了眼,那双明澈的眸子开始隐隐发红。他的心头惟余滔天的寒意,垂在袖袍下的指甲几乎嵌入了掌心。
凿凿可据的国之大义,于某些心怀叵测之辈而言,终究不过是用以朝局博弈的托词罢了。
太多事,注定身不由己,亦是——在劫难逃。
许长风在原地愣怔了会儿,旋即起身将手里的折子放回了御案上,长吁了一口气,这才恢复了眼里的清明,走到对方的身后,伸手替他轻轻揉着太阳穴。
如此,许长风心下已有了决断。
萧玄只感皮肤上触到了一阵舒服的凉意,一睁眼就看到许君泽正微微笑着,替他轻柔地按揉着颞颥。
方才的不虞便也一扫而光,他抓过了对方的手,放在唇边温柔地吻了吻,随即继续批阅起来。
“陛下,若是某日……您寻不到臣了,您会如何?”待到萧玄彻底批改完了,许长风忽然开口轻声朝他问道。
闻言,萧玄神色一滞,忽然想起了起元先生白日里来寻过许长风,顿时猜着了对方在忧思什么。
“起元先生的话,长风听听也就罢了,不必放在心上。”萧玄抬手搂过了他的腰身,让对方坐在了自己的腿上,旋即一脸笑意地看着许长风,深情且坚定地道:“长风莫要多想,有朕在,朕定会护着长风的。”
“待风波平定,朕就昭告天下,立长风为后。”
“……”
听对方这样说了,许长风弯了弯嘴角,伸手环住了萧玄脖子,轻笑着说:“陛下,臣图的又不是所谓的名分。再者,臣素来又不是那种因旁人几句碎语就郁结于心之人。”
说着,许长风便微微抬头覆上了萧玄的唇瓣,旋即将头埋到了他的颈窝里,继续补充道:“臣就是随口问问,陛下莫要会错了意。”
“……”
“若长风不见了,不论山高水远,天涯海角,朕都会来寻你的。”萧玄把玩着许长风散落在他手上的青丝,忽然贴着对方的耳畔,轻声笑道。
许长风闻言一怔,抬眸定定地看了他几息,便伸手将早已备好的酒斟了两杯,递到了萧玄的唇边:“陛下,陪臣喝几杯吧。”
“你风寒未愈,不宜饮酒。”萧玄接过许长风手里那杯酒,一饮而尽,待对方要喝时,却伸手拦下了。
“那……陛下替臣喝罢。”许长风轻笑了声,将酒杯递了过去。
美人莞尔,赏心悦目。
“好。”萧玄毫不设防,一饮而尽。
酒一杯接一杯饮下,不多时,萧玄便醺醺然了。
不知怎地,他感觉这酒比往日要烈上几分。
“阿玄,你是不是醉了?”许长风忽然靠了过来,在他的耳畔轻问。
“我……我没有……”萧玄撑着额头,用手指了指酒盏,示意自己还能喝。
“……”许长风无言喟叹了声。
“阿玄,我扶你去床上罢。”见人如此了,他便垂下眸子掩盖眼底的悲戚,将人扶去了偏殿。
强烈的醉意过后,萧玄只感觉内火焚身。此时此刻,见心上之人就在眼前,他便将人牢牢锁住,旋即倾身而上,嘴里遍遍呢喃:“长风……长风……”
“阿玄……”许长风哑声回应着,双手也抚上了对方的肩颈,一双杏眸早已变得通红不堪。那蓄了许久的泪,终究还是从他的眼尾淌下,落入发间,晕出一片湿意。
那一夜,两人颠鸾倒凤,抵死缱绻,彼此彻底释放。
翌日,萧玄醒来,身侧早已没了熟悉的温热,他慌乱地坐起身来,只看见龙榻旁放了一身叠的整齐的朝服,边上还附了两封信和一方私印。
【陛下亲启:臣自知无能,特引咎辞退,望陛下允臣之意,解官归去,勿念。
臣许长风,拜上。】
“长风,你……”
看着这廖廖几句,萧玄悲愤交加,当即就要发作,但还是忍着脾气,双手颤抖着打开了另一封信。
【阿玄亲启:阿玄,我虽为你之师,然你的才学从不逊色于我。如今,我已然将毕生所学所得尽数授予你。
日前,于沿海诸县试行的“鱼盐政令”现已初显成效,愿阿玄酌量推之。
阿玄,朝局清算尚未歇止,总有亏心之人拼了命想遮住天家的眼睛。哪怕为君者览天下权,有些时候,所见所闻甚至比旁人更少。阿玄聪慧,料想你自是明晓。
昔日,我藏于六部的耳目及麾下幕僚的名单,我已将其置于枕下,以我的私印便可任你随意调度,望善用之。
言至于此,阿玄,不如给我们彼此留一个机缘罢。
你我以十年为期,在此定下约定。若十年间,你能开创个乾坤盛世来。届时,你便一直南下。
如你我缘分未断,自然便可重逢。如若不然,你来寻我,我断然也是不会回去的。
执笔落墨,言尽魇矣。
阿玄欢笑尽娱,乐哉未央,余诚心所愿也。】
信讫,萧玄的鬓发已然凌乱地垂落在眼侧,欲言万语,却没了可诉那人,只得尽数哽在喉间。他睁着早已通红不堪的双眸,徒然地看着许长风昔日里所着的那身朝服。
狼狈且悲苦。
他深知对方的性子,既是这般说了,便没了回旋的余地,如果自己强行将他寻回,恐怕到那时,自己便会彻底失去他。
如今,便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头。
许长风说着是给他们之间留了机会,但细细想来,此番也算是诀别了。
这个国家早已积贫积弱了好几朝,想要在短短的十年间,致使天下晏然,国富民强,简直好比痴人说梦。
但终究所有人都小觑了萧玄的实力,他最后却是真真正正地将这个王朝推上了历册的巅峰。
功绩照千秋,美名传万载。
对这世间,萧玄尽了自己作为帝王的本分,便再无亏欠。他也该南下了,去赴故人的十年之约,
从此,一代明君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往事散尽,萧玄抬手拂开了许长风额前的落下的一缕青丝,笑意晏然地看着对方道:“长风,宸帝已崩。”
“这世间,从此只有心悦于你的萧玄,想同你白首偕老的萧玄。”
许长风心疼的要命,想着当年自己留下的一纸空言,对方却是拼了命地让它从虚妄变成了现实。这十年里,许长风想都不敢去想,萧玄过的是怎样水深火热,刀尖舔血的日子。
他好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回去同他一起面对。
“阿玄,苦了你了……”许长风早已泪眼婆娑,抬手捧着萧玄的脸,泣不成声,喃喃出声。
萧玄从来见不得许长风哭,抬手轻抚着他的后背,温柔地安抚着:“长风,我不苦的。我知长风的心意,离开本就是万不得已,若不让天下先平息,你我之间注定难捱。”
“好了,不哭了……”
“今日正逢乞巧节,长风何不随我出去走走?”萧玄轻轻揩去了对方眼角的泪痕,随即伸手捏了捏许长风的脸颊,在他脸上扯出个笑来。
“别闹……”许长风轻轻拍掉了萧玄的爪子,起身便准备下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萧玄弯腰替人穿好了鞋袜,旋即就将人从床上抱了起来,径直往外走去。
“你干嘛?我自己能走……”许长风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一慌,忙不迭用手环住了他的脖子,羞红了脸,低头小声嘟喃着。
萧玄听他嗫嚅着,低头亲了亲对方的眉眼,还掂了掂手中抱着的人,随即笑着在他的耳畔轻道:“我是就想抱着长风,不行啊?”
“你欢喜就好……”许长风将搂在他脖子上的双手,又紧了紧,随即将头靠到了萧玄结实有力的胸膛上,听着对方那真实有力的心跳。
他的阿玄还在的,此后还会一直在。
萧玄轻功一点,将人抱到了一处屋顶上,两人便在瓦檐中躺倒,十指相扣,卧看牵牛织女星。
趁着月色正浓,萧玄牵起许长风的手,放在唇边吻了吻,忽然轻声开了口:“长风,此生固短,无你何欢啊。”
“得君如此,我才算此生不枉。”许长风也偏头看向萧玄,粲然笑道。他的眸子里仿佛盛着尘世星河,可那璀璨的中央,至始至终都只有一人——萧玄。
“长风,我在桐溪寻了处宅子,离这不远,到时候寻个良时,我想为你补上一场拜堂。”
“我的长风,该是三茶六礼,明媒正娶,风风光光地被我迎娶进门的。”萧玄搂着许长风,看着浩淼的苍穹,轻声笑道。
许长风闻言一怔,心下触动,眼眶顿时酸了,又开始流起泪来,连忙用手背蹭了蹭脸上的湿润,心里欢喜地不行:“嗯嗯,好……”
萧玄低头就发现了对方匆忙掩饰的小动作,心疼地挑起了他的下巴,温柔地帮他吻去了眼角的泪水,旋即又覆上他的唇,渐渐加深了这个吻。
“唔……”
清风拂翠微,皓彩映鹊桥。
两人在月色下深情相吻,万千景色一时竟也成了陪衬。
此后无数人间风光,终可携良人共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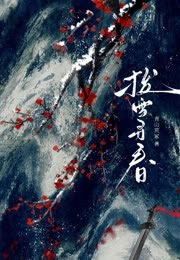




![师徒文学,但师尊在上[穿书]小说](https://img.gljjx.kouwz.com/storage/20250604/UiDKbTjgifVkrrEAlmEZ.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