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万物》一定不要错过这本小说:宴如阙在第七次轮回中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失忆的村野少年宴十三。他本想躺平当条咸鱼,却被卷入江湖纷争——各方势力为争夺"天机卷"厮杀,而他自己竟是关键钥匙。当他遇见那个总被追杀的美人公子江榷(实为隐姓埋名的萧家遗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江榷表面是个武功稀松的绣花枕头,却能随手解开宴十三身上最毒的蛊;宴十三对敌人招招致命,唯独对江榷连板子都舍不得打重。

《不见万物》精选:
三人耳听有哧啦哧啦咬啮声,只当园中小动物吃果子,再过半盏茶的时间,哈哈大笑声平地炸起,三人皆是吓得原地一蹦,就连枝丫上安静栖息的夜猫子睁开滴溜滚圆的眼珠子咕咕叫了两声,
见一人身穿破旧绀青道袍大步走来,一手里揣着好些橘子,这些橘子足有一篮筐那么多,用衣摆兜在胸前,另一手上还拿着果子,口中嚼着,这人竟不剥皮,连皮带肉一同吃将下去,吃得满嘴满须都是红彤彤的果肉,露出一口崎岖黄牙。
山茶根手指此人口中大叫道,“好哇!竟给你都吃了去!”
那人开口声音威威,“我在林子里吃橘子,听你们在这儿叽叽呱呱,便来瞧瞧是什么人深更半夜来这儿开什么茶花会?”听来竟似在斥责,教人心里不好舒坦。倒栽柯心道,此人一开口我便知他小鸡肚肠眼里不容沙,是个不好相与的人!我之脾性较之此人,还甚或可爱几分哩!这人脾性又硬又臭,但武功高强,方才他开口空气都随之震荡有波,若非是武功修至上承境界者,难有此效。
山茶根见来人腰间别着一只狭长黑布袋,黑布袋旁有一只葫芦,这葫芦有酒气,心里已将来人身份猜了个大概。
倒栽柯来了劲儿,手叉腰问道,“又是谁夜半三更在林子里又吃着这劳什子橘子?好哇!竟是你个老头儿!有意思!有意思!”
那老者眼光一转,见地上还坐着个人儿,将其面貌一打量,道,“山茶根,你怎也在这儿。”他说起话来也不是在询问或是他乡遇故旧,那一对眼睛那一张嘴,再是没有把任何人放在心上的。宴十三将此人情貌言行举止看在眼里,心道,世上也竟有这等人,他瞧他人同他人说话,也好似在瞧死物,在同死物言语。
山茶根和酒扇道人二人俱是未料到能在此时此地碰到同一个组织里的同僚,平日里,二人各行其事,从未见过面,九参便是这样,看似是一个不见天光严丝合缝的组织,但其中松松散散,其严密程度还不如路边一块冒着热气新鲜出炉的桂花米糕。
山茶根道,“怎么,这独漉大会你酒扇道人来得了,我山茶根就该种在山下?”原来此人是酒扇道人吴喆君,这下倒栽柯明白了,酒扇道人有一样本事是江湖中知之者甚少的,不是他那把名唤长洲孤月的扇子,也不是他同泉殊波的武功秘法,而是他胸腔里早没有心了。这是倒栽柯一直好奇的事情,刑天没有了脑袋照样能舞戟,可没有了心要怎生活下去。
酒扇道人道,“衢钺坊恁的小气,先给你们吃些带毒的果子,过两天再给你们可解其毒的果子,我这老头也是无聊,夜里着榻难眠,索性爬起来溜达溜达,倒给我这老瞎子见到了朱柑。”
倒栽柯听他所言吃了一惊,“你是眼睛瞎了么?我……我这老登西身躯将死,这些年我走遍三山四海,寻找那些没人用的肢体,好拼凑出一具完整的身体供我好用。”
宴十三坐在一旁只作壁上观,他心道,这老东西是死不成么?听他这话里,似乎还能复活的意思。许是意志武功未泯,但阳寿走得久了身体就自然开始腐朽。我这做徒弟的年轻人和他们三个老前辈混在一块儿,还是不开口为妙。
倒栽柯一瞥酒扇道人的胸膛,“我途径鄘都城,我朝繁华都城令老朽欣喜若狂,山林水边游玩得久了,见市井人烟也好生新奇快活!”
那小子有一双轻巧的赌博好手,这手能用来握刀挥剑写诗作画,他却用来欺骗同伴整日里赊账豪赌玩物丧志,一日我见他同友人借钱遭拒,我丝毫不怜他,只将他双手砍下。他既用不来这双手,不若老朽替他善用之!
在场的皆非什么大善大好之人,听之也未觉不适,态度平平,只当作是听过了,但倘若是菩萨心肠的,听到了免不了一番争斗。譬如那旗亭宫的陈垣礼同垂萝山庄的高垂山,这二人便是一对活宝,这二人虽武功不一,但最是喜爱悲天悯人,但若教他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施舍那些将饿死的人,又是万万不肯的。
那倒栽柯抻臂从酒扇道人的兜里拿了一只朱柑,手中一边剥橘一边嘻嘻哈哈道,“将来我就是有了这双手,还望诸位多同我斗斗牌搓搓麻将,聊以慰藉枯燥的老年生活。”
酒扇道人觑他这一双手,倒栽柯这双手青筋凸起纹路纵深,皮贴骨骨抓肉,剥起橘子来看起来双手灵巧。酒扇道人心道,哦!他这是快死了。
山茶根见这两人互相打量,“我好酒”酒扇道人之所以为酒扇道人,表面上瞧是因为他喜扇嗜酒,身边总戴着这两样东西,但越是表面的越是难以当真,总有些缘由是说不出来的。
山茶根知晓此种,心念一转道,“你好酒我好茶,不若哪天你喝酒我吃茶,咱们比划一顿如何!”酒扇道人转向倒栽柯问道,“你说我这同泉殊波厉害还是长洲孤月长势?”倒栽柯“嘿”了声道,“哪有自己同自己比划的!”酒扇道人从黑布袋里拿出一柄扇子,唰地展开扇了两下,“这便是长洲孤月。”山茶根眼瞄扇道,“你这长洲孤月怎么个比法?”酒扇道人道,“自是与同泉殊波比。”倒栽柯搓手道,“你这长洲孤月同我比如何?”说罢,从腰里摸出一柄拂尘来,正是他假扮衢钺坊童儿拿的那柄
酒扇道人看向倒栽柯道,“是了!我差点将你忘了,你这武功用不着什么合手称心的武器,衡虚派出了你这样的弟子,也是奇了怪了。”
这倒栽柯给这样烟里虚里骂一顿不见其横眉恼怒,反而手拍大腿高兴起来,“正是!正是!我正是衡虚派荡舟人门下的弟子!”衡虚派涂香长老座下四大门人,分别为荡舟人、楚狂人、山丛人以及谢情人,其中以楚狂人最为出名,楚狂人武功言行不若名号这般“狂”,反是彬彬有礼谦谦君子,使的也是衡虚派涂香一脉至纯的刹尘剑法。荡舟人行踪不定,武林中言语荡舟人或曰荡舟人业已身死也未哪知。
宴十三心道,哪有吃茶的同喝酒的比?也哪有自己与自己比?倒栽柯瞧起来不着调的模样竟是支砣山衡虚派出身?且这荡舟人的书中记载也寥寥几字,但有个弟子倒也是奇闻。这帮老前辈果是怪趣相投,凑到一块儿去了。他哪知这仨前辈明面上互相邀约,暗地里相互试探,三位老前辈虽功法相异各具所长,支砣山衡虚派居北,山茶根月杀秘诀属南边的功夫,唯独酒扇道人不知出身何处。这仨老头儿又因老顽童的性子,虽是互相打量磋磨,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胡话,话语言辞里出招拆招,但是心底已将二人引为友人。
这会儿子时将过,宴十三惦念江榷只想快些回宿舍去,因而到这时已然兴致缺缺,垂头耷脑手下薅着地上草尖,他三位老前辈越是你来我往宴十三越是困倦连连,一副要睡将过去的模样。
酒扇道人把兜里朱柑一抛,比划起招式来,一枚朱柑正是砸到宴十三的脑门,宴十三“啊”的一声醒将过来,见仨老顽童摆开架势,这是要文斗罢来论武功了。宴十三悄悄起身,退进橘子林中,果树鳞次栉比,宴十三眼皮沉沉疲倦至极,脚下步伐颠三倒四东倒西歪,素荣园中果树栽种间隔紧密,常人难以进出,便是轻功不佳者亦是磕磕绊绊,素荣园使身怀独门秘法,轻功游走出入照料自是不在话下。
宴十三这步伐看似个醉汉,实则融会贯通了倒栽柯今晚教给他的拳法掌法,这厢身躯要撞上树干,那厢脚步迟来,劲道也跟着后滞,反让身子晃过了树干,果树甚密,下一步又一棵橘树迎面,但足下步伐方迈出去,劲力前摇身子在后,堪堪贴面避了开去。走出素荣园,给山涧凉风一吹,宴十三才猛一个激灵,举目一望,吟道,“青山明月不曾空。”①
*********
江榷回到宿舍门前,见一女子身着竹月裙衫蹲在路边,离得近了才看清这女子出手救治一只狸奴,江榷一瞧这不是夏大夫么!忙在她身边落定。
这狸奴许是冲撞了什么,两只前腿骨折了,软在地上一声不吭,夏大夫身边没有带伤药,手里削四块大小合适的的木板。江榷伸手进怀里道,“我这儿有。”说着拿出一只小瓷瓶,夏大夫接过放下鼻下闻了闻,“这药可用。”遂给狸奴的两条前肢敷上药,江榷给的是金烟蜜,需以一点内力化开,这金烟蜜听起来昂贵异常,实则是略等于金疮药的寻常用药,不过多个清热解毒的功能。
二人将金烟蜜化开涂好,再以夹板绷带固定。那狸奴奄奄地叫了两声,夏大夫眉目柔和将狸奴抱在手中,走了几步又回身睇向江榷道,“你来做什么?”
夜风习习,江榷索性席地而坐,“夏大夫,我知您不以天下人命为己命,而以天下苍生万物为己任,在下愿以命相抵,若是将来有个人有不测,烦请您救他。”
夏大夫道,“这世上我最不想救的就是人,我救过的人真算来其实寥寥无几。”
那女大夫将受伤的小狸奴托入臂弯里,江榷听夏大夫如是回答,心里也不恼不怒,好似他早知会得到如此回应。江榷哂道,“但世人皆说您是济世悬壶的大夫。”
“莫要以此来压我。”女大夫轻抚着臂弯里的小狸奴,“届时我是想救能救,我自会救。若是不想也不能,那么他人即便是以命相求,在下也爱莫能助。”
江榷吁了口气道,“夏大夫说话还是这般,以命相求,自是一命换一命的事情,公平买卖,符合规矩。”
夏大夫面带笑意,“规矩是死,人是活。”神貌平淡,似是想起了什么事来,摇摇头道,“现在,我且不能答应你。但你若是替我对阵一人,并且打败他,我便全然应允。”
江榷自知说服不了,口中应下,但心里想道,也是,夏大夫向来对人命不感兴趣,我若是一味以命相抵,她反是看不上眼。夏大夫见他应允,便从怀中缓缓摸出一枚药丸,这药丸香气袭人,有霜雾缕缕,冷若冰霜,但正值夏日,反倒沁人心脾。夏大夫抬手用指甲轻轻从中对开,取出一半给江榷。
夏大夫看他服下半枚药丸道,“我与你虽非头遭相遇,但我上回救你,你欠我人情,这回哪能便宜了你。这是菘蓝丹,有去腐生肌之效,我瞧你性命之患在即,便以这法子拖住你,事成之后,我自当给你另一半。”
江榷道,“倘我一心向死,岂不是白费功夫。”夏大夫咯咯笑道,“哪里是这样,你服了半枚菘蓝丹,不仅好不了半点反而生腐毒发的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不正遂了你的意!先前我在阿霞客栈看过你一回,缘缘堂青崖阁的七步指原理其实是与七步蛇一脉相传,但治你不死反助你活下来,只是元气亏损,我给你开了四逆汤。”
江榷心道,竟是这样!那么想来我从前也是为夏大夫搭救,只是此中细节记忆不清,夏大夫为了让我二人达成交易,也是说一半藏一半。江榷索性顺势游走,转而问道,“夏大夫可否告诉在下,九参里第八人是谁?”江榷心里也没有个底,踅摸九参的事已久,但总归缺胳膊少腿,又或如七宝楼台看起来玲珑精致,拆下来竟不成片段。
“呀。”夏大夫笑着叹了口气,这中年女子的面容素淡,月色下如秋山白露,她道,
“我乃玄州人,怎告诉你鄘都的事情。”
“那看来此人在鄘都城里?”江榷摆了几颗小石子,用手指推弹着,“日日夜夜在鄘都,我竟浑然不知。”
夏大夫轻笑连连,“但这事情告诉你也无妨。你且留意留意,大筐速运。”江榷在所认知的人物一一做了排除,俶尔脱口道,“小顾?”夏大夫颔首,江榷问道,“夏大夫常年蛰居崔锦,最远也不会出玄州,怎会知晓?”夏大夫微笑道,“我知你有疑问。当年我出鄘都城救了一只小狸奴,正是小顾养着的那只,黑漆漆的小狸奴。”
江榷点头,确然,大筐速运的老板顾吹云养了一只狸奴,这狸奴浑身黢黑,四肢肉垫都是黑如煤炭,两只眼珠子灿若星子,小顾爱它怜它,到处把它带在身边抱在怀里,逢人就说这是他的心肝宝贝儿。旁人摸他的心肝宝贝一下都不肯,江榷一次趁小顾不察,偷摸两回,那小狸奴圈着尾巴瞧他一眼,三两步抻着身子走到他腿上盘躺下。顾吹云这小心眼的追着江榷一顿揍,二人绕宅跑了两三圈。
江榷撇着嘴,想起那只黑色的狸奴,酸溜溜道,“小顾真是好命,我哪里像小顾哥哥这般啊!”
夏大夫掩袖笑道,“倒也不必这般妄自菲薄,个人且有个人的缘法。小顾当年接了那只狸奴心生欢喜,我急着出城也不作久留。倒是小顾停我下来喝了一杯茶,说了一些好似闲言碎语的话,我一介赤脚大夫哪里懂这些。”
江榷听她话中有话,急忙问道,“还请夏大夫告诉在下。”夏大夫道,“这些事我本是不愿同旁人说与,一来我一介大夫闲云野鹤不问世事惯了;二来此事也与我无关多。但祸从口出,说多了也于我没什么好处。”
江榷思索片刻道,“小顾没有理由刺杀我和我师父斟月夫人,还有师父的妹妹枳月夫人,她二人关系向来不合,其实也犯不着分开刺杀。我以为是是如仙子,竟也不是她。”江榷手下弹了一颗小石子,顿了顿接着道,“这人用弓箭弩一类武器,且准头极妙百步穿杨,是如仙子即便也想取我小命,但她御弓之术可谓是七窍里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夏大夫缓缓点头道,“小顾同我说一些话,其中关于‘九参’的,是这样一句话:‘九参’不过是九位顶天立地的好手参与其中,谋划但各司其职的组织,所以叫‘九参’。”
江榷道,“‘九参’也就是九位好手共同参加的意思,是也不是?”
夏大夫道,“正是。小顾还说,‘九参’无论江山社稷动荡与否,它一直都在,大到皇位更迭,小到在路边买一只胡饼,玉宇楼台大街小巷,‘九参’的影子无处不在。”
江榷单手支颐撇过脸去,片刻笑道,“我以为是人参的‘参’。”又道,“怎么像是苍蝇似的,见缝就钻无孔不入。”心想道,这些话可能是夏大夫借顾吹云之口说将出来也未哪知。
夏大夫听他这般形容,知他是牵涉进去恼恨不已,哈哈一笑道,“确然如此,但我等寻常百姓不知者也就无知无觉罢了。倒是你小子,知道了太多也不怕惹来杀身祸害。你先前求我将来倘是事出有因,救他人一命。”夏大夫说至此,口中一停,叹口气道,“下回若是你自己,我可救不了。”
江榷转而问道,“夏大夫,你可有什么愿望?”夏大夫道,“我想有个庄子,和小缀一起,庄子里跑满了狸奴……”江榷还待说上两句,一转头,夏大夫人带着狸奴已然走远,反见师弟宴十三正立在几步开外,“咦”了声道,“师弟缘何半夜不睡?”宴十三归来见师兄坐在宿舍门庭,吃了一惊,他二人一前一后东奔西走,未料撞了个正着。
宴十三想到出门前看到桌上留下的一枚挂佩,窗户大开不知给刮跑了没有。江榷起身望了望天边,云海苍茫,明月浮沉,宴十三顺势张开双臂,揽一川冰轮于怀。
二人仿佛回到了鄘都城的别院里,时而一里一外地坐着立着,彼时江榷为避人耳目扮作女子,至今宴十三都不清楚是何缘故,这会儿突然想起便问道,“师兄那时究竟何事要易作女子?”江榷一听闻的是这事,也不欲瞒着直截解释道,“倒也不是什么事,只是那时我莫名遭人悬赏,彼时我还是彻玉楼楼主,未免殃及楼中他人,便易容一番。”
宴十三点头道,“悬赏之事可有眉目?”江榷道,“只知悬赏了我的脑袋一百两,出自何人、悬赏范围等等全然不知。后来我同师父商议,把彻玉楼盘了一百两出去,随师父回木霁山庄。”宴十三想了想道,“师兄,若我哪天穷困潦倒,还借师兄的脑袋一用。”江榷笑开了眼,“好说,你尽管借去!”说至此,话便断了,山风吹一池绮縠,鼓起二人的衫袖,宴十三道,“我当你是一个人坐在路边默默哭,心想何等伤心事想不开来。”
宴十三打着哈欠,江榷也跟着打一个,江榷道,“就是想起了‘小顾哥哥’。”宴十三没由来地发酸,却心想,江榷提这人必是有缘由。宴十三问道,“哪个‘小顾哥哥’?”江榷道,“是顾吹云,大筐速运的老板,这家伙是吃皇粮的。”
经这一提醒,宴十三神貌了然,江榷见状心道,他倒是记起来了?宴十三道,“我先前进城寄送包裹时,倒是碰到过,顾老板身上常伴着一只通体漆黑的狸奴。那黑狸奴闻到我身上的血的味道,不叫也不动,只是静静地瞧着我。我先前家里开屠肆,若是寻常的小动物,总是要对我呲上一呲。”
师兄弟二人说着话,风动飘忽,回环错迂,宴十三的发丝被风吹乱,江榷伸手去拨。宴十三转过脸来边笑边说着话,江榷想起夏大夫的愿望,不禁说道,“将来倘是有机会,我就要养只狸奴,有半大不小的院子给它闹腾。”
宴十三道,“我看别院合适,届时可以养狸奴。”江榷点头道,“是啦,别院空间大,够它来回上下。”宴十三道,“回去就养。”又掰着手指道,“白的黑的三色花的棕色的,一个花色来一个。”江榷道,“哪里那么多狸奴跟你回去。”宴十三道,“去抓呗,城里郊外山林里,总有一只愿意跟我回去。”江榷笑笑,背过身去手去,朝着宿舍走几步,见宴十三仍立在原地,催道,“走罢,明日还有明日事。师父说我俩已在独漉,莫要懈怠了练武。”
宴十三顾着风顾着星子顾着风把云海吹来,他闻一闻,好像江榷身上的味道还在耳鬓边,他旋过身来跟在江榷身后,口中打着哈欠懒懒回道,“是了,师弟的武功还需长进。”
宴十三知道自己的头发偏硬,一拨就顺,哪像是江榷的发丝,又细又软。
*********
春碧收到信已是两日之后,午时, 展信读之,知檀荷、清水二人姐妹情仇,又遭人仇杀,惨死在独漉山门口。常人之情本应大哭或大笑,哭是人之生死悲恸之情自然而发,笑是仇恨得报终有时乖厄之笑。春碧,这白沙留月的年轻女子总管,只将信读完,面上笑意浅浅,信手把信纸搓进香炉里,瑞香袅袅,枯木生碧。
春碧,如今名唤白孜颖,她立在花厅删枝剪叶,其余庄丁侍女立在厅外,白孜颖却两眼无神,直把两三根手指剪得血淋淋的,像一只只洞开的流血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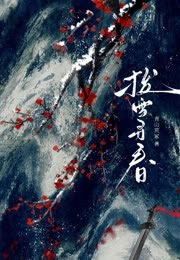




![师徒文学,但师尊在上[穿书]小说](https://img.gljjx.kouwz.com/storage/20250604/UiDKbTjgifVkrrEAlmEZ.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