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归蛊》正在连载中。泰和九年北境战乱,战神元凌退敌后,竟获赐婚 “残废王爷” 魏长卿,朝堂嘲笑他屈尊,王府疑他是卧底。新婚夜,元凌持剑抵魏长卿咽喉,质疑其残疾是伪装,魏长卿则反讽他谋杀皇亲会掉脑袋。无人知晓,轮椅上的魏长卿愿为元凌重燃战火,中蛊的元凌甘为他守国门。赤燕关激战、旧仇败露后,新帝登基,魏长卿求和离,元凌持枪拦阻,魏长卿却以天煞孤星为由劝他离开。

《同归蛊》精选:
“残月引饲蛊…透骨钉锁魂…魏长卿!”余呈渊彻底压不住心中的怒意,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那蛊纹未消的手腕狠狠怼到他眼前,“你当年自请卸甲,说什么旧伤复发…原来是被这鬼东西折腾得差点疯魔自戕?”
魏长卿抿紧了唇,目光罕见地闪过一丝狼狈,别扭地转向一旁。他原本无意让余呈渊知晓一切。
“怪不得…怪不得这些年你死盯着我药王谷的凤凰血!”余呈渊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吼道,“原来你早知这‘狂血’需要凤凰血压制!”
“可你知不知道…凤凰血只能救急!若想根除,非‘蛊引’不可!你这疯子…当真是疯透了。透骨钉锁着你的神魂,强行压制蛊毒反噬,每一次动用内力都会生不如死…你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宣王殿下那点微乎其微的良心,此刻终于艰难地发酵出一丝名为“愧疚”的东西。
毕竟曾经的余谷主,顶着“医圣”名头,向来奉行“医不叩门,死不强求”的放羊式行医准则——爱治不治,爱死不死。
却硬生生被他逼成了个操碎心的老妈子,但凡他魏长卿有半点不配合,这位谷主就能当场表演一个“叽嘹暴跳”,比他自己毒发时还要吓人几分。
“余圣手,消消气。”魏长卿的声音罕见地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像绷紧的弓弦终于泄了一丝力。
余呈渊狠狠瞪着他,胸腔止不住地上下浮动,仿佛要把肺里的火气都喷出来,“我真想撬开你这颗石头脑袋看看,里面除了算计和找死,还剩什么。早知你会把自己折腾成这副鬼样子,当年就该让你烂在战场上!”
他嘴上骂得凶狠,动作却未停,一把拉过魏长卿的胳膊,细细查看着他手臂上的纹路。那东西如同活物,在烛光下微微搏动,带着不祥的灼热感。
“姓魏的,”余呈渊皱着眉,神情很是严肃,“你给老子一句准话,你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
帐内陡然一静。
魏长卿侧脸的轮廓在炭火的映照下忽明忽暗。向来巧言令色宣王殿下竟会因着一句话而沉默了。
‘想活?想死?‘
这问题于他而言,太难了…
魏长卿十二岁初上战场,少年意气,只觉天地广阔,生死不过是马革裹尸的豪迈点缀。小伤小病,旁人的“珍重”于他不过是无关痛痒的絮语。
后来因着那场变故,他成了世人眼中的‘残废‘后卸甲归京。这副皮囊是残破还是完好,他何曾在意过?
最黑暗的那几年,他被刻骨的仇恨淹没。于他而言,最好的归宿不就是拖着仇人一同坠入地狱,在烈火中同归于尽吗?
余呈渊猜对了,最初的他,从未想过“之后”。
那些日夜啃噬心腑的恨意,早已将他锻成了一柄只为复仇而生的凶器,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在乎粉身碎骨的“疯子”。
病在心里,不在身体。
可偏偏命运弄人。
事到临头凭空冒出了一个元凌,一巴掌将他既定的轨迹推离了原来的方向。人一旦心生妄念,想求的就更多了——好比眼下他会想着,若能有幸得偿所愿,再剩下一点不残不病的年月,留给那人。
这妄念如野草疯长,会使人方寸大乱。
因而在听闻元凌“狂血”发作、命悬一线时,魏长卿彻底乱了。
什么隐忍,什么伪装,什么大局,统统抛诸脑后!不惜暴露“装瘸”的真相,也要星夜兼程赶到他身边。
他终究是生了贪心。
“你的意思我都懂,”魏长卿的声音带着沙哑的妥协,目光落在余呈渊的手指上,“所以之后……还要余圣手多费心……”
帐内药香氤氲,这近乎示弱的姿态,竟将余呈渊满腹的怒火和数落硬生生堵了回去。他捏着金针的手一顿,最终化作一声沉重而认命的长叹。
“罢了罢了…遇上你,算我余呈渊倒了八辈子的霉。”他语气依旧不善,但怒意已转为深切的忧虑,“不过,你为何会知晓他体内有‘狂血‘?”
“陛下想故技重施,倒是让我省去了不少麻烦…”魏长卿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心口,“那位‘赏赐‘的小玩意儿也算有点用处。我察觉到了他体内也有与我相似的存在…因而让你提前准备了凤凰血,以备不时之需。”
“…抱歉,蛮人的巫蛊之术我了解太少,帮不上什么忙。但据我观察,你和他……这‘狂血’发作的样子,似乎不太一样?”余呈渊始终皱着眉。
“嗯。”魏长卿闭了闭眼,压下心头的波澜,“他的蛊种,深植心脉。而我的……在后颈。”
“位置不同,差别何在?”余呈渊追问,医者的探究本能盖过了其他情绪。
“后颈之蛊,多是成年后强行种入,如我这般是外侵之毒。而心脉……”魏长卿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则是幼年,乃至……在母体之中,便已生根。是自血脉带来的诅咒。”
“元将军的蛊毒是娘胎里带来的?”余呈渊猛地抬头,金针在指尖一颤。
“这些年我多方打探才知,北齐之内曾有一支名唤厄诺的部族,其族人最是精通巫蛊之术。当年先帝在位时,对他们便多有忌惮。”
炭火噼啪爆开火星,魏长卿的笑声隐隐透着嘲讽,“当他得知厄诺族中有有一种能激发人的潜能,将人变得悍不畏死的‘狂血蛊‘后,他老人家便起了别的心思。”
“为了能独占秘术,他派人灭了整个厄诺族。后来更是丧心病狂地将这秘术用在了自己的亲人身上。”
“你怀疑,当年长公主之死是因为…先帝?”余呈渊头回听他提起宫闱秘史,“但你之前明明说是叶家…”
魏长卿摩挲着青瓷盏沿,茶汤映出他眼底猩红的蛊,“区区一个叶家,怎可能轻易便将手伸进镇北侯府。若非有上头人的默许,谁能动得了镇北侯。”
余呈渊心知他说的有理,但若事实真的如此…他不经抬头看了眼魏长卿。他一个外人听了这些尚且感到心寒。魏长卿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你说的这些…又与你那小将军有何牵连?”余呈渊有些疑惑。
“因为当年他们都失败了。”魏长卿盯着手中的茶杯,杯中的茶水在他的注视下开始不安分地涌动。“于是他们便想到,若是让蛊种在母体中自然孕育,说不定会培养出一个完美,能被为他们所控的‘狂血‘…”
“这怎么可能?我所知的‘狂血’十分霸道,许多成年人尚且承受不住。寻常胎儿又怎能活下来?即便侥幸存活,经年累月受蛊毒侵蚀,心智岂能如他这般……正常?若他早已被那些人控制,你又怎会……”
“我确实怀疑过他。”魏长卿坦然承认,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冷的青瓷茶盏边缘。茶汤微漾,映出他眼底深处一丝猩红的蛊影。
“还是因为赐婚?皇帝想用他监视你?”余呈渊皱眉。
“不止。”魏长卿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横空出世,力挽狂澜,接下这人人避之不及的漠北军帅印……桩桩件件,都太‘巧’了。”
巧得像是精心布置的棋局,而元凌,就是那颗最关键的棋子。
“那你当初还答应赐婚?直接拒了岂不干净?”余呈渊听他这么说,很是不解。
“拒绝?我怎么拒绝?”魏长卿轻蔑一笑,“我这皇帝表兄,疑心病比他爹还要重上三分。赐婚是试探,试探我这个‘残废’是真是假,也试探这位‘天降将星’的忠心,究竟是不是给他的。”
余呈渊脑中灵光一闪,“你方才说‘怀疑过’……意思是现在你不怀疑了?为什么?”
这问题如利箭一般,让魏长卿身形几不可察地一顿。
为什么不怀疑了?
这问题他也曾在无数个寂静的深夜叩问自己。
是新婚那夜,隔着梅林薄雾,望见那人舞剑的身影?落英纷飞如血,剑光凛冽如霜,那道不尽的寂寥,竟与多年前边塞孤城上的自己……如出一辙。
是北旭山晨雾未散,那人伸手将他拉上马背,温热的掌心将缰绳塞入他手中。少年将军卸了银甲,红衣被山风鼓荡成帆,在他耳边低语,“北旭山断崖向东三十里,有我留下的人……”那眼底,是毫无保留的赤诚,是将身家性命相托的信赖。
还是那一日酒醉,那人眼底燃着两簇灼人的火,逼问他,“魏长卿,你为何不信我?”
那一刻,魏长卿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酸涩难言。他不忍看着那人眼底的炙热化为冰冷的灰烬。他有多久没如此靠近过这般温暖的月光。
这千般情衷,万种心绪,他只想……说与一人听。
“在你给我寄信之前,”魏长卿收敛心神,声音恢复一贯的冷静,“我不知他身负‘狂血’。也未曾将奉安侯府与当年之事联系起来。”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幽深锐利,“但如今看来,当年参与那疯狂计划的,不止叶家。奉安侯府……甚至当年的陆家,都脱不了干系!”
余呈渊倒吸一口凉气,当年之事的真相,恐怕远超他想象。但魏长卿今日的“坦率”,透着不寻常。
“你会把这一切告诉我,究竟……意欲何为?”他警惕地问。
长佩文学网(https://www.gongzicp.com)
长佩文学网(https://www.gongzic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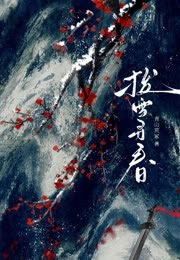




![师徒文学,但师尊在上[穿书]小说](https://img.gljjx.kouwz.com/storage/20250604/UiDKbTjgifVkrrEAlmEZ.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