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谢所著的双男主纯爱小说《叶阳大人升职记》值得一看,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叶阳辞误吸御猫被外放当七品知县,一路从基层官员摸爬滚打,凭借手段杀回京城,朝中势力一手抓,还有老相好并肩。郡王秦深隐忍多年成功夺位登基。众人以为叶阳辞要失势,没想到新君就是他老相好。这俩一个以为勉强直男,一个表面冷淡实则痴汉,恋爱事业两不误。

《叶阳大人升职记》精选:
议事厅灯火亮如白昼,一叠叠户口黄册、赋役白册与土地鱼鳞簿被源源不断搬运进来。
叶阳辞端坐案前,向旁伸出一只手,书童李檀立即将沉香木制的家传算盘,乖巧地放在主人手上。叶阳辞一手算盘,一手账簿,运指如飞,圆珠相撞的清脆响声不绝于耳。
厅门外的文吏们眼睛都看直了。江鸥在旁观望,不可思议地感叹:“叶阳大人一边珠算,一边心算,看簿册一目十行,计数据分毫不差……莫不是个演算天才!”
激动之下,他茶也不吃了,觉也不困了,盘腿坐在案边,伸着脖子专注地看,时不时帮忙递送和翻页。
叶阳辞全神贯注,不知时间为何物。
夜色由浓转淡,天际靛蓝褪色成鱼肚白,院落中的路灯被早班的皂隶逐一熄灭,而议事厅的灯火与算珠声彻夜不绝。路过的胥吏与衙役们,投向议事厅的目光从不解,到震惊,再到钦佩万分,散入无数细碎的言语中:
“打了整整一夜的算盘……”
“这些簿册积压多年,都是蛛网灰尘。上头说每年都要照刷文卷,磨勘卷宗,其实根本没来看过……”
“知县大人这是要清算整个县的旧账?”
“咱们这位新上任的大人,可了不得啊!”
当然也有不少心虚恼火的,悻悻然嘀咕:“能算得清才怪,装模作样罢了!”
随着最后一声算珠响声落地,叶阳辞将整理出的数据誊在纸上,长吁了口气。他一夜未眠,精神却仍抖擞,面颊上泛着微微的红晕,在晨光中容色鲜妍。
江鸥双眼熬出血丝,盯着桌面上新写成的青皮簿册,薄薄的一本,却是全县的命脉所在。
叶阳辞手按青色封皮,起身拉伸了一下肩臂,平静地道:“年年寅吃卯粮,白条透支。财政赤字折合白银足足两万一千五百八十七两八钱四分四厘,几乎等同于本县十三年税收。”
江鸥听得头皮都麻了。
“本官昨日来时,在渡口驿登高而望,见荒田无数。今年夏税怕是也缴不齐六成,不知又要去哪里东挪西凑。”
江鸥长长地叹了口气:“年年难过年年过,总能活下去的。”
“你只想着活下去?”叶阳辞反问他,目光在满室看不见的风雪中飘过来,使他背生战栗,是沮丧,也是期待。他听见叶阳大人说,“可我想的却是赚钱。不仅我得有钱,县衙得有钱,农夫、工匠、商贩……也得有钱。我想要田茂嘉禾,山覆果林,店铺鳞栉,商船如织,太仓禀足,家家户户钱柜盈余。”
江鸥惊呆,喃喃问:“这……真能实现吗?”
叶阳辞微微一笑:“不勉力一试,又怎么知道呢?”
议事厅外,唐时镜双手抱臂,后背倚着墙,听了许久。离开之前,他从怀中摸出一个油纸包,丢给端着空脸盆走出门来的李檀。
李檀手忙脚乱接住,险些连盆也掉了。他张牙舞爪问:“怎么又乱扔东西!”
唐时镜没理他,转身走了。
李檀骂骂咧咧地拆开油纸包一看,是五个罗汉果。昨日这玩意儿有效,主人的嗓子舒服多了,可惜一熬夜,今早又开始肿痛。这包罗汉果真是及时雨,李檀转怒为喜,自语道:“这唐巡检看着像个刺儿头,其实还挺会拍上官马屁。”
他喜滋滋地去找药罐来熬罗汉果汤。
待到果汤熬好,连同早膳一起端来时,姗姗来迟的郭县丞与韩主簿终于来拜见新任知县。李檀撇了撇嘴,把早膳一盘盘放在桌面,对叶阳辞道:“主人,县丞和主簿在门外廊下候见。”
叶阳辞先喝了半碗罗汉果汤:“不急,吃饭要紧。来,坐下同吃。”
李檀摇头:“罗摩准备去集市采买日用品,小的也想同去,免得他粗枝大叶买漏了,还要多跑一趟。”
叶阳辞知道这话不假,但李檀年少好动,爱凑热闹也是真,便应了。
慢条斯理用完早膳,叶阳大人拿茶水漱过口,整理完衣冠,方才气定神闲地走出屋子。
廊下的郭三才与韩晗早已等得不耐烦,正要行礼,却见叶阳辞连眼角余光也不给他们,径直走过去了。
韩晗一急,在他背后唤道:“知县大人!”
叶阳辞驻足,回头,侧脸在阳光下好似壁画中的诸天。“阁下哪位?”他冷淡地问。
韩晗尴尬道:“下官夏津县主簿韩晗。”又示意身边人,“这位是夏津县丞,郭三才郭大人。”
叶阳辞上下打量他们,端着架子评点:“老,不好看,忘性大,还没礼貌。”
郭三才和韩晗一同愣住。他们设想过初见时的各种交锋,却万万没想到,竟是这么一句近乎荒诞的揶揄。韩晗涨红了脸,忿然道:“知县大人年纪轻轻,就对长者出言不逊,未免太过孟浪!”
郭三才倒是比他沉稳几分,拱手道:“先前是下官二人怠慢了大人,还望大人恕罪。今后下官定当将功补过,为大人效劳。”
对方服软,叶阳辞也不想这么快就撕破脸,便问韩晗:“韩主簿呢?”
韩晗没奈何,只得跟着作揖道歉:“下官失礼,冒犯知县大人,大人恕罪。”
叶阳辞说:“你二人加起来将近百岁,比寺庙放生池里的老乌龟还多吃了几年饭,当知上下尊卑。昨日之事就此揭过,今后不得再犯。”
郭三才强忍被比作乌龟的恶气,捏着鼻子应了声“谨遵知县大人教诲”。韩晗问:“那大人与两家族长见面一事……是否交由下官来操办?”
叶阳辞一脸无可无不可:“行啊,那就有劳了。对了,地点选个风雅些的园子,最好足够宽敞,多设些席位,本官要好好结识一番两家的青年才俊。”
他说完转身就走,剩下两个须发斑白的“老乌龟”,站在原地恨得牙痒。
叶阳辞换了一身轻便装束,策马独行,短短数日跑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以及城外的几个乡、里。
夏津县管辖范围不算大,可耕种的土地却不少。二十年多前战乱未平,民众大多出去逃难,以至城郭废弃,田地荒芜,春燕归来无栖处。而今休养生息,朝廷也酌情减少了田税和人丁税,但整个县好似沉疴新愈,仍未缓过劲来。
斜风细雨中,叶阳辞头戴箬笠,身披蓑衣,蹲在田间地头与一个歇息的老农夫闲聊。
“开春了,今年麦子好种吗?”
老农夫叼着俗称“柳叶尖”的绺子烟,吐了口白雾:“小哥要是问田,土够肥,毕竟以前埋了不知多少尸体。我老头胆大,不怕动不动刨出骨头,还是好种的。”
“可晚生方才一路走来,见十田九荒,可惜得很。”叶阳辞叹气,“看来不是田薄,是人少哇!”
老农夫点头:“打仗时全县死得死,逃得逃。人越少,粮越少,粮越少各家就越不敢多生,也不知什么时候能重新热闹起来。”
叶阳辞沉吟:“本地短时间是没法大量繁衍人口了,除非……移民屯田。但这是国策,并非一地一人所能主张。”
“小哥,你是县学的生员吧,怎么不去读书,和我一个种田老头有什么好聊的?”老农夫吧嗒吧嗒抽着烟,“你好好读书,将来去做官,就不用吃劳作和徭役的苦了。”
叶阳辞笑了笑,反问他:“做官为了什么?”
老农夫一愣,说:“过上好日子?”
叶阳辞点头,又摇头:“是要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他起身,从袖中摸出个小布袋递给老农夫,“耽误老人家干活了,这是晚生的一点补偿。”
老农夫接过来掂了掂,听铜板响声估摸百文,满脸褶皱都展开了:“小哥出手阔绰,日后定能高中。”
“承您吉言。”叶阳辞拱手告辞,走出田埂,把栓在树干上的坐骑缰绳解了。
他上马,朝着县城飞驰而去。行至城东门外,狭窄破旧的拱桥禁不住连日雨水冲刷,就在他的马蹄下歪斜,开裂,随后轰然坍塌。
马受了惊,险些掉进自家县城的护城河里。叶阳大人于危难中力挽狂澜,拯救了坐骑,把箬笠都挣丢了。好容易安抚好马儿,他仰头看天。蒙蒙细雨洒在脸上,他喃喃:“新建一座石拱桥,小一点的,至少三百两银。”
他每年俸禄四十五两,另加铜钱一百八十贯以及部分稻米;新上任朝廷给拨“道里费”三十两;柴薪银、廪给银之类津贴加起来就算六十两吧,一年也不够修一座桥。
积蓄是有一些,但不能都花在修桥补路上,这个千疮百孔的县城,到处都要修缮,再说,也不该他掏自己的积蓄来修,没这个道理。
更何况县衙里只有县丞、主簿,以及无品阶的杂佐官(如典史、巡检等)由朝廷发俸禄,其他胥吏和衙役都得靠他用本县收入来养,要用钱的地方多得去了。
叶阳大人眼下愁钱,一颗想赚钱的心更是膨胀到了极致。
整个高唐州,谁最有钱?
临县武城、恩县,情况比夏津稍好一些,但也是穷。州城所在的高唐要富庶得多,但知州大人管辖地盘大,消耗也大。
有没有什么不事生产,空领俸禄,田庄众多,仆役成群,尸位素餐,不劳而获……的狗大户,可以让他打打秋风?
好像还真有一个。
——高唐王,秦深。
叶阳辞回想七日前,自己与高唐王在夏津城外渡口驿的一面之缘。那张冷傲而写满晦气的脸,在他眼中慢慢放大,简直可爱得有如送财童子一般。
叶阳大人在春雨中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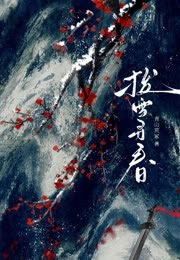




![师徒文学,但师尊在上[穿书]小说](https://img.gljjx.kouwz.com/storage/20250604/UiDKbTjgifVkrrEAlmEZ.jpg)



